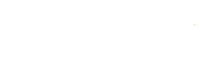第二四九窟
景点评级:暂无评级景点地址:这是开凿于北魏与西魏交替时期的洞窟。平面呈方形,覆斗顶,属于殿堂窟的类型。在莫高窟,这种形制始见于十六国晚期的北凉洞窟,跨越了北魏之后,又为西魏所继承,并成了其后各代造窟的主要形式。这个窟的东壁虽已坍塌,但其余诸壁壁画保护完好。壁画內容除了以佛,菩萨等组成的说法图以及千佛等外来题材外,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内容。特别是窟顶四披,既有佛教的阿修罗和摩尼珠,又有传统的神话题材东王公、西王母和四神等道教形象。这显然是道家思想和外来的佛教思想互相融合的反映。 道教是中国的本土宗教,起源于汉代,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之后,当时的崇信者很快就把它和道家拉在了一起,主张“会通两方教理”,进而“合黄老浮屠而为一”。从此,佛道融合的思想开始普遍流行。从北方到南国,从中原到边陲,佛道杂揉,共为一体的现象不但大量出现于祠堂和墓葬,也反映到了佛教艺术中来。敦煌虽然处地边远,但这里从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方,佛寺道观长期共存,于是道教的题材便也进入了佛教一统天下的石窟,大大地丰富了洞窟壁画的内容。 这个窟的顶部是莲花藻井,四顶的上部画满了天宫诸神,下部是山林野兽和狩猎场面,构成整体境界,各顶又各有主体,形成相对独立的画面。 西顶的主体画是阿修罗(非天),是印度神话中的恶神。赤身四目、四臂,其中二臂上举,手擎日月,“足立大海,水不过膝”,身后耸立着须弥山,以示阿修罗形体高大“身过须弥”。须弥山腰有双龙护卫,山上有巍峨的宫城,这是佛教所谓三十三天的忉利天宫,是帝释天居住的地方。 东顶的主体画是力士捧摩尼。摩尼珠就是如意宝珠。这种题材在早期洞窟里比较多见。 南顶的主体画是西王母。西王母身空大袖襦,乘三凤车。上有重盖高悬,前有御车仙人,还有乘鸾,扬幡持节的仙人作前导。车旁文鳐腾跃,白虎护卫;车后旌旗招展,天兽尾随。 北顶的主体画是东王公。东王公身着大袖长袍,乘四龙车,御者持缰待行。车上华盖高悬,旌旗飘扬,前有乘龙持节方土引导,后有天兽开明尾随。这幅画与南顶构图类同,相对成双。东王公和西王母分别趋龙车凤辇向同一方向飞行,在天花旋转、云气缥缈中形成了浩浩荡荡的巡天行列,大有“遨游太空”“穷观天域”的气势。在相同内容的壁画中,这是场面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一组画面。 在窟顶还画有许多其它道教形象。九首人面、人头虎身的怪物叫“天明”,这是居住在昆仓山下的民族部落以虎为图腾的形象。还有守护四方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四神。这些神灵都是远古氏族的图腾,在封建社会中变成了道教的护卫之神。在四顶还穿插了风、雨、雷、电等自然神的形象。那“头似鹿、身有翼”的是司风之神“飞廉”。 首、人身、鸟爪、口喷云雾的怪物是雨师计蒙。虎头人身、臂生羽毛的怪人正张臂旋转连鼓,以鼓声象征着雷鸣,这是雷公。兽头人身、手持铁砧、砸石发光的是辟电。裸体披巾、臂生羽毛、“千岁不死”、“ 羽化升”天的是长耳羽人。还有人首鸟身的仙灵以及中国式的大力士乌获等形象。这些神灵都是用“想象和借助于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产物,是人们美好理想的化身。 四顶的下部是人间的景色。有山峦、树木、水池、花草、还有各种动物以及狩猎的场面:翱翔的仙鹤觅食的山羊,漫步山野的灰狼,蹒跚而行的白熊,拴缚在树上的双马等,形象之生动逼真实为其他各代洞窟所不及。特别是北顶那只野牛,虽然只用简练的土红线勾勒了牛的形象,并没有敷彩上色,但把野牛受惊后有腾空奔逃的同时回首惊望那一瞬间的动态神情描绘得惟妙惟肖。使一头雄健暴烈的野牛跃然壁头。野牛后面是一个跃马飞驰、身姿矫健的猎人。他正要跨越山岭追赶野牛,突然身姿矫健的猎人。他正要跨越山岭追赶野牛,突然身后扑来了一只凶猛的老虎。在这紧急关头,猎人临危不惧,借跃马腾空之势回身一箭向虎射去。身手不凡,令人叹服。这是一个高难度的动作,画家准确地摄取了这一惊险的场面,犹如抢拍下了一幅惊心动魄的狩猎镜头。再后面是三只拚命奔逃的黄羊,骑马追来的猎人如风驰电掣,引箭待发,大有利箭出弦,瞬息可得之势。生动地刻画出了善于奔跑的黄羊和猎人慓悍勇猛的形象特征。 北披处东端下角,一头野母猪领着一群小猪不慌不忙地在山间漫步,似乎在觅食,一副悠然闲散的样子。 东顶的那只猴子,举手于额前,遮挡住强烈的光线抬头远望,那机灵的特征颇具人味。 在南顶东下角的山林中,两只恶狼正在堵截一只山羊。山羊无处可逃,一副绝望的可怜相,生动地刻划出了狼的凶残和羊的软弱。 这些以山水为背景的画面在表现的同时也具有很强的装饰性:山峰的排列象梳齿一样整齐,人物形象比山高大,这就是画史上所记载的“群峰之势,细饰犀栉”,“人大于山”,这是魏晋以来中国绘画的显著特征。敦煌早期壁画完全继承了这种传统。




写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