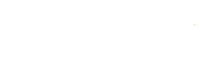申文波梦到自己回到家,和妻子、儿子说说笑笑。
醒来时,阳光透过铁窗照了进来,四周传来听不懂的说话声。
清晨7点,1000多个犯人从7个牢房涌出,到院里排队接水洗漱,之后,生火煮饭或是领救济餐,找阴凉处蹲墙根,直至下午4点半收监回房,等待黑寂寂的夜。
6月30日,这是申文波在马达加斯加监狱度过的第510天,一起被困的还有8名中国船员、4名孟加拉船员、2名缅甸船员,均来自中国货船FLYING,2019年3月因非法入境被判刑5年。
中国货船FLYING上的15名船员在狱中的合影。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狱中,他们亲历过暴乱,被狱警拿枪指过,也被遍地的蟑螂、老鼠、木虱子咬过,最难忍受的,是心里的煎熬。
5月中旬开始,马达加斯加(以下简称“马国”)新冠疫情加重,截至当地时间6月30日,该国累计有2214人确诊。船员们身处疫情中心塔马塔夫市,这里已经全面封锁,医院人满为患。6月12日,监狱来了一群穿防护服的医生,先给监狱消毒,之后给7号牢房中出现症状的新犯人做检测,并将其中25人集中隔离到1号牢房——船员们则被换到了有80多人的3号牢房。他们向大使馆求助后,监狱方回复说,7号房出现了登革热。不过,有狱警私下告诉他们,已有3个犯人3个警察感染新冠。
被困住的船员们忧心,自由还没等到,就被病毒找上。
监狱岁月
申文波至今记得第一天进监狱的情景。
那是2019年2月6日,大年初二。一大早,他们15个船员被3个警察叫下船,挤上两辆皮卡,送进监狱。
眼前的大院,破败如电影中的难民营,几间平房散落,犯人们衣衫褴褛,有的光着脚,有的在生火做饭,直盯着他们看。
破败的监狱大院
船员们一下懵了,猛拍监狱门,喊着要见监狱长,要联系大使馆。越来越多犯人围过来。
警察见状,持枪爬上墙头,呵斥他们散开,犯人们一哄而散,他们也吓坏了,不敢再闹。
当天下午,监狱负责人把他们召集到操场开会,让他们服从管理,再闹就要处罚他们。作为惩罚,当晚,一些船员被关进条件最差的牢房,第二天才统一分到1、2、3号屋。
7个牢房中,1号屋是“VIP牢房”,通风,较为凉快,只住二十多人,关押的是有钱“有关系”的犯人。2、3、7号屋为中等牢房,一间住100多人,需交2万马币才能入住。另外3个牢房每间被隔成3层,住了300多人,都是没钱的犯人,晚上轮流排队睡。
牢房大多只有50余平方米,没有床铺,犯人睡草席或水泥地上,人贴着人,翻身都难。
监狱牢房
船员们花钱买来垫子、褥子,给牢头小费,空间才稍大一点,没想到引起部分犯人的不满,冲他们唱歌、比手势,双方差点打了起来。
塔马塔夫全年高温,气候湿热。牢房里,闷热混杂着汗臭,蟑螂在地上走,壁虎在头顶爬,老鼠跳到身上,吓得他们哇哇大叫,引来一阵哄笑。
申文波在2号屋住了一个多月,全身被木虱子咬出疙瘩,还起了痱子,找监狱长求情才被换到1号屋。水手李以印被毒虫咬伤,起水泡后留下黑疤,痛痒难忍。其他船员也出现了皮肤溃烂、化脓、拉肚子等症状。
白天,他们在院里放风,看马国犯人踢足球、打篮球,偶尔下象棋、打牌,很少说话,因为心情压抑。
和外界联系,起初只能偷偷借用警察手机,5000马币(折合人民币约10块钱),能打5分钟,后来1万马币用两小时。去年9月,大使馆出面协调,监狱才允许他们用手机。他们托当地华人餐馆老板买了个二手手机共用,狱警帮忙保管,每天能用3个半小时,今年开始隔天用一次。
华人餐馆每天给他们送饭,两个菜,一瓶矿泉水,有时也捎些生活用品、药品。吃饭费用船东出,老板经常抱怨船东欠钱,又联系不上人。
狱中的其他犯人,没钱的只能吃救济餐,一点木薯,或是米饭加煮烂的豆子;有点钱的,找警察买米和菜,生炉做饭。
船员发现,找警察买东西时,一条烟经常少一盒,一瓶可乐到手只剩半瓶。有时警察伸手要钱,五千或一万马币,要到后热情地喊“friend,friend”。还有船员被忽悠给狱警买了两个1000元的手机,这样才能“出去活动活动”。
丢钱是常事,有的警察会暗中调查,找到小偷后把钱私吞了。水手长孟范义有一次丢了17.5万马币,警察找出小偷后,监狱长要走3万,两个警察各要了2万……到他手上只剩下8万。
去年7月,监狱里发生一场暴动。狱警惩罚一个吸大麻的犯人,犯人跳墙逃回牢房,警察劝他出来不听,他的几十个追随者跟着起哄。第二天早上,二十几个警察持枪,驱赶所有犯人回牢房。
被警察拿枪指着,船员们都吓坏了,跟着人群往牢房跑。闹事的犯人朝警察扔石头,警察开枪扫射,击穿了一名无辜犯人的手掌,最后揪出那伙人,打得浑身是血。
狱中还有精神病犯人,每晚嚎叫,抢衣服穿;羊癫疯犯人口吐白沫,往人身上撒尿;还有的犯人据说有艾滋病,船员们不敢靠近。病死、被打死的犯人也有,就躺在卫生室门口,苍蝇围着。
上个月,又有两名犯人死了,船员们慌了。
新冠疫情3月20日蔓延到了马达加斯加,确诊病例不断上涨。
监狱里,狱警们戴上了一次性口罩,家属禁止探监,7号屋专门腾出关押新犯人,偶尔有人对垃圾桶、污水沟喷消毒水……但船员们依旧担心,狱警每日进出监狱,常常拿掉口罩,聚集聊天;新犯人靠其他犯人送饭送水,仍有接触;还有的犯人会出去做劳工,保不准把病毒带进来。
船员们想出去隔离,使馆建议他们聘请律师提交保释申请;找船东老板杨建丰,也没什么进展,只能跟监狱长申请找间空房隔离,也没被批准。最后,花了2000块钱(人民币),所有船员换到了1号屋。
到5月中旬,塔马塔夫首次出现死亡病例,确诊人数激增,政府征用了3个场所收治无症状感染者。
船员家属都很担心疫情。
船员们相继发烧,其中两位高烧了十来天,吃不下饭,整夜无法入睡,吃药打针也不见效。
5月25日,一名船员在狱中写的信。当时船员们无法使用手机,只能将信交给帮他们送饭的当地华人餐馆老板,再转发给家属。
手机不让用了,他们只能写信,托送饭的餐馆老板转发给家属,家属向大使馆求助。大使馆请医生到狱中为船员看病,开了些药,这才逐渐好转。在大使馆的协调下,船员们重新用上了手机,不过每次只能用一会儿。
申文波后来听说,那两位去世的犯人死于胃病,而非新冠肺炎。但狱警私下透露,监狱里有人确诊了,有几位狱警好几天没来上班。
中非在线微信公众号也披露,5月底,塔马塔夫监狱一名犯人核酸检测为阳性。
6月初,又有两名新犯人出现了严重的新冠肺炎症状,被送进医院,船员们为此胆战心惊,除了洗漱、吃饭,寸步不离牢房,睡觉也戴着口罩。
他们不敢告诉家人自己的处境,担心死之前还能不能和他们团聚。
危险航行
一切源于那次远航。
2018年8月3日,申文波从香港登上FLYING船。上船前,他在船讯网上查过资料,这是一艘1997年建造的老船,97米长,17米宽,在货船中不算大。船东为福州民丰船务有限公司,实际控制者为香港莲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FLYING停泊在塔马塔夫港口。船员符伟刚弟弟2019年4月赴马国探监时拍摄。
此前,他在航运在线网上发布简历,大连华商船务有限公司派遣他上船,职位为大副,月薪13000元。跑船10年,这是他第一次当大副。
上船后头两个月,FLYING从香港装废铁运往越南,再装木薯回东莞,往返于三地之间——过去两年也主要是这条航线。
直到10月2号,他们接到船东指令,去新加坡加油,之后到马达加斯加装木材,3个月后返回。
“突然接到指令跑其他航线,这个很常见。”申文波说,船员上船后必须服从船长指令,装什么木材船东没说,他们也没过问。
10月7日,FLYING从新加坡驶往马达加斯加。船上17人,除船长和船东代表外,大多第一次登上这条船。
中国货船FLYING上的15名船员名单(2019年统计)。
年过五旬的轮机长蔡拥军、水手长孟范义,想再干几年,挣点钱养老;厨师陈旭东第一次上船,他本是装修设计师,想出海散心;二水李以印为了给女儿赚奶粉钱,已经上船9个月了,他不想去非洲,但合同期没满,公司没找到接替的人,不让他下船……
之后20天,FLYING斜跨印度洋,一路天气很好,风平浪静。船员们三班倒,每天工作8小时。休息时,看电影、玩游戏、打牌、钓鱼,或者在甲板上跑步、锻炼。
10月26日,FLYING在马达加斯加东北部附近海域抛锚。那里距陆地20余海里,天晴时能看到陆地、岛、山,海水十分清澈,鲸鱼会游到船边玩耍,一有鱼群过来,船员们纷纷出来钓鱼,他们钓到过一条大鲨鱼。
抵达之前,船长曾发邮件询问航次指令、装货计划,船东回复说公司还没谈妥,让等消息。
申文波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有一次,从印度装棕榈壳到日本,卸货后没有新货,只好在日本领海漂航,被日本海岸警卫队用甚高频喊话驱逐。还有一次去加拿大,计划装粮食,船到了,货没谈好,漂航20多天后,改装焦炭运到美国。
一周后的11月初,一艘灰白色的小船朝他们驶来,自称是马国海军,要求停船检查。
船长向船东报告,船东说,不能确定对方身份,而且上船会敲诈勒索,“直接驶离就行”。
小船追了一个多小时没追上。申文波觉得有点奇怪:当时船在外海,“我们从来没接受过在外海的船检查”。
也有船员怀疑是海盗船。蔡拥军就遇到过海盗,那是2006年运白糖到索马里,半夜两点,两艘快艇一直追他们的船,喊话不停船就要开枪。停船后,上来了8个海盗,强行把船开到索马里抛锚。所幸,白糖的货主是当地走私头目,船员们没有遭受虐待,被劫持46天后,公司给钱了结此事。
为了防止海盗登船,公司每月会组织防海盗演习,拉铁丝网、架消防水枪、设藏身的安全舱等。
FLYING继续在离马国100多海里的深海漂航。西南洋流吹拂下,船自动往马国方向靠,每次离岛五六十海里,他们就往外开远点。
到11月底,一天上午,一架灰绿色两翼飞机在船上空盘旋,发出嗡嗡声。船员们好奇地朝飞机招手,只见飞机带着闪光,两三分钟后,飞走了。
申文波开始有些起疑。进港装货时间一再推迟、取消,而且船刚到马国海域就关闭了AIS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不符合航运国际公约中AIS 24小时开启(除非进入海盗区)的规定。再加上又遇到了执法船、军机,他担心航次有问题,于是写了份声明书,表示是合法船员,绝不做违法的事,要求再进港要看文件手续,其他船员也纷纷签字。
船东回复他们,马国负责装货的货主正在办手续,“航次绝对是合法的”,手续不全不会再进港。
船继续漂航了半个月,12月15日接到返航回国指令,船员们一片雀跃。没想到,次日晚上,又接到指令掉头回马达加斯加,并将船开到指定位置,与护航船汇合,代理到时候会上船。
申文波察觉有问题,他召集船员开会,要求船东出示航次指令、代理信息、货物信息等材料,被拒绝后,他提出离职,船东批准了。
发现航次有问题后,申文波提出离职,被批准了。
船长于天财显然也发现有问题,但他还是按指令行事,偷偷找船东签了份《个人利益保障协议》,上面写着,他如果触犯法律、被扣押或入狱,船东每月要付他2.2万元的工资,留下法律污点的话,另给30万补偿。
船长于天财偷偷找船东签订了《个人利益保障协议》。
2018年12月17日上午,船到达指定位置,那里隐约能看到岸上山峦起伏,申文波后来回想,当时可能在马国12海里领海范围内。护航船并没有出现,船东让继续等待,他“抓紧联系”。
此时,一张抓捕大网正朝他们收拢。
海上追击
又一艘船驶来,声称是马国海军,要求停船检查。时间是2018年12月18日凌晨两点左右。
船东下令驶离,FLYING掉转航向,小船一路紧追不舍,速度略快。
申文波被船长叫醒去起航后,和船长、船东代表、二副一直待在驾驶台,心里紧张又害怕,祈祷着不要被追上。船东安慰他们,“会派直升机来救你们。”
沿马岛海岸线逃跑约4个小时后,两船相距不到500米了。马军发出警告,再不停船就要射击了。
密集的枪声划破深夜,驾驶台玻璃顷刻间被击碎。申文波仓皇逃到二楼卫生间,那里有钢板,安全一些。
FLYING驾驶台上的玻璃都被击碎了。
睡梦中的船员被惊醒了,惊慌失措地跑出去看。一见这情形吓坏了,直往卫生间、机舱躲。
逃到二楼角落的二副,被穿透水密门的子弹残片打中屁股。船东代表的左腿被子弹击中,肚子上留下子弹擦过的伤口。他心想,完了,这下要死在印度洋了。
紧接着,火箭筒打到船上,警报声四起。符伟刚去机舱查看,见一层的玻璃震得粉碎,心里很害怕。
枪击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停顿之后,水顺着甲板哗哗地往下淌,船员们以为下大雨了,几个胆大的探身张望,发现有高压水枪对着船喷射。
船上的电路很快短路,舵机失灵,船失控了。船长见状,举手投降,冲小船喊:“不要开枪了,我们出来。”
船员们举着手到甲板上列队。申文波这才发现,追击他们的是一艘拖轮,十几个身穿迷彩服的士兵正拿枪指着他们。
放引水梯后,5个士兵登船,有的光着脚丫。他们搜走船员身上的手机、现金,让他们在船头抱头蹲下,之后去生活区搜查,出来时,脚上穿着船员们的运动鞋。船员房间里的手机、电脑、现金、衣物等也被拿走,塞进包里,用绳子顺到拖轮上。
当天,FLYING被拖轮拖着往马国港口驶,12月20日清晨,到达塔马塔夫港口。“命保住了。”船员们松了口气。
靠港后,几十个马国政府官员登船检查,询问船长关于船东的信息、此次航行目的等,还有当地记者录像拍照。
之后,船员们被困在船上,轮流到警局接受审问,两个警察守在船梯口。
被困原因,马国士兵登船时告诉他们了——FLYING 2015至2016年到马国走私过红木,马方怀疑这次也是来走私的,船还没到,就接到了情报,因此先前派出了执法船和军机。
船员们一下懵了,他们大多2018年才登船,不了解这条船的历史和船东公司状况,也不知道这次是要拉珍稀红木。只有船长和船东代表在这条船上工作了4年。
一位曾在FLYING上工作过的船员接受财新网采访时透露,杨建丰2014年买下这艘船,当时船名为MIN FENG,2015至2016年到马国走私过几次,没办合法手续,不进港,只在锚地装货,2016年红木被香港海关查获,2017年他将船喷漆改造,改名为FLYING。
在船员们的追问下,船长承认之前去马国装过3次红木,每次船东都说手续办妥了,直到2016年红木被香港海关查获,他被带走调查,才知道报关手续文件是假的。那次,货物被扣了,但船员和船东都未被追责,他猜测“红木(走私)集团背后的势力很强大”。
两位去年4月赴马探监的家属,也看到了当地华人手机上MIN FENG船2015年从海里吊红木的照片,当时船身蓝色为主,而FLYING红黑色为主。
2015年,当地华人拍到了MIN FENG从海里吊红木的照片。
杨建丰告诉船员,手续不全是因为马国合伙人欺骗他,船到了装货地才有手续,未料他们没到就被抓了。
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杨建丰承认FLYING是去拉红木,不过是普通红木,而非濒危物种。被问及2015和2016年是否去过马国,他先是否认,之后松口说去那边拉过鱼货。记者再三追问有没有去马国走私过红木,他笑了下,说“我真的不清楚。”
在枪击中受伤的船东代表和二副,当天被交通艇送到医院救治,半个月后回到船上。2019年1月17日,两人被律师和警察带走,以出国治疗为名偷偷回国。
这让其他船员看到了希望。他们觉得船东代表是所有船员中责任最大的,“他都能回家,我们也能回家。”
未料20天后,他们等来的是入狱——两名船员私逃激怒了马国政府,导致其他船员被投入狱。
艰难求救
15个船员都在等待船东营救。
船东找了位当地律师,先是告诉他们,春节前能回国,后来变成了一审完能回。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派领事协助处理这件事,几次到监狱看望船员,要求马方公正处理案件,保障船员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督促船东负起第一责任人的责任,聘请律师,同时保障船员在狱中的生活、药物需求。
2019年3月,马国法院一审判决17名船员非法入境及拒绝服从罪,判刑五年,每人处罚金5250万马达加斯加法郎;船长和船东代表因开船逃逸罪,多6个月刑期。
船员们难以接受。船东辩解说,律师拿钱跑了不办事。
申文波觉得不公,被抓前他已经离职,却也被判刑了。马国以涉嫌走私红木为名抓捕他们,在船上没发现证据后,以非法入境定罪。申文波认为,非法入境的是货船本身,应当由船东和船长担责。船员们都有船员证,按照国际海事法律规定,不应算非法入境。
另外,船进入马国没有提前汇报,“那是船长的问题,不是我们船员的问题。”船员们在法庭上的证词、提交的证据都没被采纳,判刑有无充足证据支持,他们也不知情。
船员家属到福州找船东杨建丰夫妇,前两次,杨热情接待,说他正在全力解救,他们最晚七八月就能回国。在家属的要求下,他补发了2019年1月和2月的工资。3月之后的至今没发。
这之后,他一直告诉船员,在和马国谈判,马国不开条件,也没有人出来和他接洽。
去年8月二审前,家属第三次去福州找他,杨避而不见。家属向当地政府、公安局求助,也没见到人,无奈而归。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杨建丰态度大变,经常不接电话不回微信。
到2019年11月,二审维持原判,马国对私逃回国的两位船员发出逮捕令,不过,在国内的他们至今安然无恙。
杨建丰在家属群现身,让船员们不要在意结果,说马方已经给出方案,他也已经接受,下周三会签文件。等到了周三,他说改成了下周,月底,下个月……他口中的出狱日期不断推迟,理由是,马国政府要的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价格,双方没谈妥,需要重新谈判。
二审后,杨建丰在船员家属群说判决结果和船员回国没有关系。
船员们感觉被欺骗了,在网上发求助信,给大使馆写信,还提起了上诉,至今没什么消息。
家属们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并到马达加斯加探监,还给海关总署发过举报信,请求调查FLYING进出港的历史记录,彻查其走私情况,追究船东责任。
能想到的办法全都做了,“但谁也帮不了”。他们想不明白,作为船舶第一责任人的船东,为何没受到任何制裁,没人去调查他。只有大使馆督促船东亲自到马国谈判,杨建丰不敢去,想找当地人办,又不敢先给钱,怕被坑,但不给钱对方不办事,担保人也找不到……事情陷入僵局。
家属咨询过海事律师,律师建议先起诉船东,讨要工资,其他的赔偿很难,因为证据较少,并且当事人都在狱中。
大使馆则建议他们聘请马国当地律师打官司。
中国驻马达加斯加大使馆工作人员回复船员家属,建议他们起诉船东。
“我们已经穷到这种程度了,还怎么到马国聘请律师?”一位船员家属说,船员大多来自山东、吉林、江苏等地农村,本就家境不佳,如今失去顶梁柱,更是雪上加霜。除了不停地找船东,找媒体求助,他们别无他法。
他们希望劳动、海事、公安等政府相关部门,提供一些帮助,帮忙督促船东,也希望有海事律师帮他们打官司。
6月11日,杨建丰告诉澎湃新闻,他已经请律师为船员办理保释,“这次大使馆直接参与一些事情,应该没什么问题。”
不过当晚申文波告诉记者,杨之前一直推说没有律师电话,记者采访后,他才发来一个,他们打过去,对方说不知情,挂断了。他们发现,这个电话竟是杨建丰之前提到的拿钱后没办事就消失了的人。
期盼回家
申文波看过一部电影,因为飞机失事,一个男人落到荒岛上,为了回家,他吃活鱼活蟹,想尽一切办法让自己活下去。两年后,他如愿回家了,心爱的妻子却已嫁作他人妇。
“我觉得这个结局一点都不好。”34岁的申文波,第一次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和自身的渺小无力。
刚被抓时,船员们一度瞒着家人,怕他们担心,也觉得很快就能回去。
入狱后,厨师陈旭东心绞痛发作,给家人写过遗书;轮机长蔡拥军“很多次想越狱,想自杀”;一个缅甸船员的女友提出分手,小伙嗷嗷大哭,剃了光头。
大管轮徐泽进瘦了20多斤,他错过了女儿的婚礼,觉得特别愧疚。妻子在工厂食堂干活,每月2000元,要供女儿读书,还要借钱还房贷。
三管轮符伟刚骗母亲自己在马达加斯加看着船,船卖了才能回。每回和母亲通话,他都要控制好情绪,怕被察觉。母亲隔一阵就问他弟弟,“你哥这次去的蛮久呀。”
十几年前,孟范义做生意失败,欠下巨债,独自挣钱还债,做过很多临时工,听说船员赚钱,才在2016年考下海员证。他觉得自己是棵小草,为了生存,有太多无奈。
知命之年遭此打击,他心有不平,“我没有触犯法律,不觉得可耻,就是觉得冤屈。”有时,他会到监狱外的小教堂坐一会儿,祈祷早日回家。
“老婆说等我回去她就不干了,她快撑不住了。”36岁的李以印在电话中哭了。妻子在县城杀鸡场工作,朝五晚八,每天要将几万只杀好的鸡放到指定位置,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女儿哭着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快了快了,再等爸爸几天。
狱中,他每晚醒两三次,白天经常头疼,像得了抑郁症一样。他说出狱后再也不想跑船,只想开个小饭馆,多陪家人和孩子。
申文波原本拥有一个光亮的前途。在这条船上干完后,再上一条船做大副,他的工资将涨到2万6。出事前他和妻子刚在市区买房,计划着过一两年买个车。
如今,一大家的压力落到妻子身上。她到商场打工,月薪2000,每月还3000元房贷,还得给丈夫寄些生活费,实在捉襟见肘。公婆都刚做手术不久,没法干活,现在小儿子上幼儿园的钱都拿不出了。
她很少跟丈夫诉苦,申文波却宁愿她像过去那样多叨叨几句。奶奶去世、两个儿子出生、父亲摔伤做手术,他都不在家;家人生日、节假日,也常常因为在船上没信号,无法送祝福。申文波觉得亏欠家人太多。
今年生日前一天,母亲语音时叮嘱他煮两个鸡蛋吃,“监狱里能煮吗?”
“能。”两人都哽咽了。
用手机的时限到了,他匆忙挂了电话,不知道电话那头的母亲哭了多久。
两个儿子在院里用泥巴给他做了个生日蛋糕。他想起离家前,大儿子抱着他哇哇大哭,他逗儿子,“爸爸在家天天管着你打你,有什么好的。”
“你天天在家打我也行,不要走。”
最近,申文波又梦到了家人,梦中,妻子脸上泛着红云,两个孩子拉着她的长裙,朝他走来。他安慰自己,离回家又近了一天。
去年12月,申文波儿子给他写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