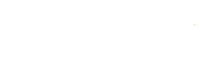二
凌晨已过。
一辆奔驰房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驶。
开车人正是魁魁,他两手搭在方向盘上,脸色比古墓里的干尸还冷漠,一丝表情也没有。连续驾驶六个小时,眼皮开始打架,这时节,到了年底,又是深夜,路上车辆稀少,开车反倒容易打瞌睡。
王曦坐在副驾座位上,望着夜幕,一言不发,脸色愈发阴郁。
魁魁叹了一口气,点燃烟,抽了一口。
后舱宽敞,沙发上坐着一个少年,手拿铅笔,面对画架,神情专注,他闻到烟味,大喊着:
“烫、烫。”
少年名叫王子,是王曦的儿子,个头不高,身体拙实,围着画架开始转圈子,两手痉挛般揉着、搓着,脸儿憋得通红。
王子患有亚斯伯格症,智力水平相当于三岁儿童。小时候,他被烟头烫过一次,从那以后,见到抽烟就紧张。
王曦走到后舱,关闭舱门,坐在儿子身边,柔声呵慰:
“你忘了?咱俩可都说好了,十天画完。你算算时间,还能画完吗?听话,赶紧画,等到家了,正好画完,妈妈给你打分。”
闻不到烟味,王子安静下来,两眼紧盯着画纸。
画纸上是王曦的头像,乍一看,几乎就是打印出来的真实大照片。绘画行里的人,把这种画法叫做照相写实主义。
王子掰着手指头计算时间,算了一会儿,才知道今晚就该交画,可他觉得,头发部分仍未画完,心里又急了,原地转起圈子,喊道:
“妈妈,妈妈……”
“不急,”王曦安抚着,“你想想,咱们走的时候,是不是收拾了一下午行李?这不就耽搁时间了嘛,对吧?听妈妈话,赶紧接着画,明天交画就行。”
王曦说话很慢,仿佛是从字典里把一字一句抽出来。因为只有这样,王子的智力水平才能理解。王子慢慢笑了,露出儿童才有的那种神游天外般的表情,拿起画笔,重新画画。
回到前舱,王曦关闭舱门,打开坤包,掏出一部粉红色旧手机。
魁魁一看到手机,立刻问道:
“今天又来微信了?”
“嗯,六点钟发来的,”王曦看着手机屏幕,“你猜,下一个轮到谁?”
魁魁摇摇头。
“猜猜吧,就剩两人了。”
“胡小缇?”
王曦把手机屏幕转给魁魁看,上面写道:十天内,杀胡小缇,河阳县文华苑2-1-201。
魁魁重重地拍打着方向盘,嘴里衔着一句骂人话,眼看着就要骂出来。
寒风啸过,奔驰房车驶上山路,连续转弯,护坡上长着几株丑悴的小树,车灯刺亮,照得小树惶恐不安,胆怯发抖。
元旦那天,也就是1月1号,这部粉红色旧手机突然冒出来,通过微信发来一个文档,题名为《阳鑫集团犯罪证据举报材料》。随后,又连续发来限时杀人指令,并且警告不许访查,若不遵从,立刻公布材料。材料中举证确凿,一旦公布,王家、阳鑫集团就彻底完了。想到这里,魁魁忍不住了,一连串骂道:
“妈的,妈的,他妈的!”
车辆左转北迤,驶上是一段直道。前方大山横亘,隧道笔直穿进山体,千岭山一号隧道的红色大字清晰可见。
王曦想查是谁在威胁自己,却不敢查,无从查,来不及查。短短一个月来,连续收到指令,已经杀了三个人。接下来,还要杀,什么时候才算完?一种绝望感从她的骨头缝里往外冒,胸中憋了一口闷气,张开嘴,轻轻长吁出来。
魁魁更是没有办法,仿佛独自摔跤,无力可使。不自觉间,脚踩油门,车速加快,问道:
“曲直身上能查出来线索?”
“我哪儿知道?试着看吧。”
“我通知厉老六吧?”
王曦有气无力地说道:
“嗯,我休息一会儿。你记住,千万不敢轻举妄动,将来要是出了事儿,一概与你无关。”
魁魁看着粉红色手机,愤恨至极,两手微抖,又气,又怕,又不服气。就算是天下最强悍的人,被对手捏住了睾丸,也只能乖乖服从。
“我还能活多少年,我死了,王子咋办?”王曦闭上眼睛,身体靠下去,“家里很多事儿,将来你得尽心。”
车驶进隧道。
魁魁腾出一只手,从裤兜摸出手机,翻找厉老六电话号码,手机滑落,掉在脚边,低头去捡手机,脚下松劲,车慢下来,向右偏去。
后方有车,跟入隧道。
奔驰房车减速,占了右边车道,后车司机见左道空出来,也不刹车,反而加速,一打方向盘,准备超车。
魁魁捡到手机,再把车向左靠,听到一声长笛鸣响,一看后视镜,有车直冲过来,赶紧扔下手机,向右靠去。
二车擦身而过,刹车声呲呲乱响,前车屁股扭了几扭,斜横着,停在百米外。
王曦睁开眼睛,喊道:
“撞上没?”
魁魁知道并未撞上,应了一声,松开刹车,慢慢向前开去。
前车下来三个年轻男人,跑到司机车门口,拉开车门,扶下一个姑娘,姑娘一下车,腿就软了,蹲在地上起不来。
二车靠近,魁魁将车停在后面。
一个穿着T恤,圆脑袋后面梳着一条小辫子的矮胖家伙跑过来,冲到车门前,喊着:
“你他妈找死呀!”
小辫子骂完话,回头瞧,开车的姑娘勉强站起身,脸色煞白,刚要迈步走,又蹲下去。小辫子心中更怒,见魁魁把车窗降下,露出了头,挥手就是一耳光。
魁魁脸上生疼,一伸手,握住了小辫子的手腕。
“放手,魁魁,”王曦拉开车门,迈步下车,“赶紧放手。”
小辫子往后用力,魁魁一松手,小辫子倒退几步,摔倒在地,站起来,喊着:
“你敢动手?给我下来,下来。”
王曦绕过车头,拦住小辫子,嘴里不停道歉。
小辫子一把推开王曦,嘭一声,王曦的脸儿结结实实地撞到了车厢上。
魁魁伸头看,见王曦蹲在地上,手捂着鼻子,血从手指间流出。啪一声,自己的脸上又挨了一耳光。他抓住小辫子手指,身体往后一坐,把对方胳膊带到车里,反关节一掰。小辫子手指生疼,一边哎呦、哎呦地喊着,一边大骂着。魁魁再一探手,抓住那根辫子,三绕两绕,擒住了对方。
小辫子的两个同伙儿跑了过来,围着车门,干着急,打不着魁魁。
魁魁听小辫子骂个不休,手上用劲,把小辫子脸儿抬了起来,摊开手掌,迎面拍在鼻梁上。小辫子蹬、蹬、蹬退了几步,坐在地上。两个同伙见有空隙,伸拳就打。魁魁挨了几拳,用车门一顶,挡开二人,迈步下车。
王曦捂着鼻子,喊着:
“魁魁,别下车,不敢动手。”
开车的姑娘跑了过来,蹲在小辫子身边,哭着喊道:
“哥,你、你流血了。”
王子打开车门,也哭喊着:
“妈妈,妈妈。”
小辫子嘴里又黏又湿,气喘不出来,一张嘴,喷出一口鲜血,低头看,鼻孔里一条血柱子直射下去,他爬起身,呜噜呼噜喊着,又冲上来。
三人围着魁魁,一顿乱拳乱脚。
魁魁紧靠车门,身体半蹲,两条胳膊护着上身,眼睛瞅准了小辫子,抬起膝盖,直磕小辫子肋下。
一个同伙儿的见小辫子倒地,对另一人喊道:
“抄家伙。”
二人迅速跑到车后,打开后备厢,翻找起来。
小辫子倒在地上,两手拽着魁魁裤脚,刚一用劲儿,肋下疼不可止,手一松,晕了过去。
魁魁到车前,被王曦拦住。
对方二人转过身来,一个戴眼镜,一个是瘦子,眼镜拎着日本军刀,瘦子挥着高尔夫球杆。二人一看魁魁,足比常人高出一头,心有怯意,互相看了一眼,各自闪开,形成犄角之势。
“老公、老公,”姑娘跑回眼镜身边,指着躺在地上的小辫子,哭喊着,“你看我哥、我哥……”
眼镜推开姑娘,冲着瘦子一点头,二人挥刀、挥杆冲了过来。
魁魁躲开军刀,则躲不开高尔夫球杆,他趁着瘦子发力未满,急向前去,胳膊架开高尔夫球杆。
当啷一声,军刀砍在奔驰车头。
魁魁抓住球杆,一脚侧踢,正中瘦子胫骨。瘦子哎呦一声,松开球杆,倒在地上。魁魁转身时,眼镜正挥刀赶来,举刀连续劈砍。魁魁拖着球杆,借着姑娘身体,一一闪开。随后,他端平球杆,一步步逼了过来。
眼镜见魁魁手里有家伙,心里慌了,脸上冒出一层汗珠。
一杆一刀,恰好接触上。
姑娘喊着:
“老公,你快跑。”
眼镜把军刀往魁魁脸上一扔,扭头跑到车旁,拉开车门,一头扎了进去,摁下反锁键。
魁魁追到车前,拉不开车门,挥着球杆,砸着车窗玻璃。几杆下去,玻璃裂成了蜘蛛网状,围着汽车,转圈砸了起来。一个月来压抑的怒气,全都发泄出来。
姑娘以为眼镜会被打死,撒腿就往隧道外跑,手里拿着手机,还未按键,嘴里先大喊起来:
“警察,警察……”
车的挡风玻璃砸出了一个大洞,眼镜躲在后座,手按车门,随时准备逃。
王曦先把王子送上车,这才捂着鼻子,赶来劝住了魁魁。
魁魁扔下球杆往回走,附身捡起军刀,一看,是把好刀,尚未开刃,坐回车上,将刀靠到门边。
姑娘刚出隧道,回头看,奔驰房车开来了,她以为要撞自己,慌忙往右跑,一条腿撞栏杆上,摔了个七荤八素,顾不得疼,也顾不得捡手机,在野地乱闯一气,哭喊道:
“杀人啦,杀人啦!”
峭风夹杂着哭叫声,中宵听来,极其凄厉恐怖。很难想象,人的胸腔中竟能发出如此声音。
奔驰房车路过“欢迎进入河阳县”的大牌子,攀爬山道,到达最高点,小城就在脚下,灯火闪烁,一枚焰火升到空中,无声炸开,散成数点星光。
“打电话,”王曦一边哄着王子,一边擦拭鼻血,“让厉老六动手,别误了时间。”
魁魁拨通电话,说道:
“厉老六,听到没?”
“哦。”
“这次是在家门口,你抓紧。”
“哦。”
“地址,我就不说了,人你也认识。”
“哦。”
“是胡小缇。”
厉老六未回答。
“喂、喂,”魁魁看着手机信号满格,“听到没有?”
嘟、嘟、嘟,厉老六把电话挂断了。
三
胡小缇三个字在曲直的手机屏幕上闪动。
曲直接通,问道:
“缇姐,有什么指示?”
“屁指示也没有,后天我去市里开会,顺便去车站接你。”
“我打车就行,年底了事儿多,你别耽误……”
“别废话,就这么定了。你替我给于薏薏、曲绮带个好,我这儿正彩排节目呢,”胡小缇的话音里夹杂着音乐伴奏声,“不多说了,我挂了。”
千岭山铝锌矿业集团成立于1956年,是国家“一五”计划的重点项目,当年,它是全国最大的开采铝锌矿石基地,繁盛时,人口近十万。九十年代,国际市场开放,进口矿石不仅价格低,且质量更高,同时,几十年的过度开采,矿石资源濒临枯竭,生产成本更高,企业没法干,只能连年裁员,职工或下岗、或调走,大多数人都分散到了全国各地。现如今,只剩下三万多人口,企业半死不活地耗着,胡小缇就是这个企业的工会文体部干事。
曲直放下电话,看着妻子于薏薏,说道:
“小缇姐接咱们。”
于薏薏很丰满,像只鹌鹑,大眼睛,小鼻子,面相文静,坐在地板上,忙乎着往行李箱里塞衣服,抬起头,训斥道:
“眼睛里就没活儿呀,全让我一人干!”
曲直家是两室一厅,客厅小到不能再小,兼做书房、餐厅,地上摊开了两个行李箱,就连扔根针的地方都没了,他绕过行李,说道:
“刚才,你还嫌我弄得乱,不让我管。”
“说你不对呀,”于薏薏嘴不饶人,“你就不会干好点?”
这个家,于薏薏说了算,曲直从不和她争吵,都是鸡毛蒜皮的事儿,争来吵去纯属浪费时间,毫无意义。于薏薏的唠叨,他索性当做没听见,把手机放在餐桌上,去了卫生间。
于薏薏发现,自昨天以来,曲直行为鬼祟,读书时,眼睛总是看着手机,还把手机倒扣在桌上,微信也调成了静音。这会儿,手机就在身后,拿起一看,恰好有微信,屏幕上有一行文字:
“晚六点,黑松白鹿见。”
发信人名叫Emma,看头像,是个漂亮女人。
曲直走来,见手机在于薏薏手里,装着若无其事,问道:
“有人找我?”
“Emma是谁?”于薏薏性格愣,不转弯抹角,“干吗约你?”
“哦,”曲直接过手机,慢条斯理地编谎话,“请我们剧组吃饭,王曦的手下,替老板感谢我们。”
于薏薏两眼紧盯曲直,一丝表情也不放过,曲直低头看手机,刻意避免眼神与自己接触。她判断,哼,撒谎,肯定在撒谎,说道:
“我也去。”
“行,人多热闹。”
“算了吧,不去了,那多碍你事儿呀?”
“我发现,你这人,”曲直终于抬头了,强辩着,“我都不能和其他女人有正常来往了。”
于薏薏没理他,走去阳台收衣服,暗下决心,找机会,查他手机。
曲直眼睛跟到了阳台,说道:
“你不是一直要买大衣吗?正好,你带着曲绮去商场,连吃饭带买衣服。对了,给曲绮买一双AJ,吵吵着要了半年了。”
于薏薏想起来,之前,曲直曾经说过,男人们一旦有外遇,会不由自主地启动心理防御机制,给妻子买礼物,以抵消自己的道德亏欠。那个词叫什么来着?对了,叫做仪式与抵消。
“省着点吧,”于薏薏又一想,曲直拿回来九万块钱,或许就是体贴自己,说到花钱,心尖就疼,“房贷、曲绮的学费,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曲绮呢?”曲直拿起手机,往女儿房间走去,躲闪着于薏薏,“半天不出来。”
于薏薏一边干活儿,一边观察,曲直两眼不离手机,疑心又起。
曲直敲着女儿房门,无人应答,推开看,曲绮躺在床上,头戴耳机,捧着手机在追剧。
***
一个多月后,曲直将会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和哪个女人睡都行,唯独不能和Emma睡。而现在,他却一无所知,一步步走向Emma。
天色已暗。
出租车停在亮马河桥边,曲直下车,沿岸而行。
河面厚冰逾尺,几个少年在滑冰嬉戏,两岸枯树成行,一叶不挂,少年的声音无遮无挡,传得很远。
亮马河南岸是各国大使馆,上空飘着各色国旗,北岸有一排低矮房子,有餐馆、酒吧等,黑松白鹿餐厅就在其间。
曲直一边走,一边想,和Emma认识一天多了,微信聊天足有两百多条,她主动请我吃饭,啥意思?我没钱,长相也忒普通,扔到人堆里,基本上没人看。
走了百十米,曲直又没信心了,掏出手机,查看微信聊天记录,以分析、判断Emma态度。
中午前,曲直抱着试探的态度,发出一条文字:
“我酒品、人品都不好,喝多了,容易出事儿。”
Emma回复了一个打脑袋的表情。
紧接着,曲直发出一条相当露骨的文字:
“你是我见过最美的女人,任何一个男人,见了你都会动心。”
几秒钟后,Emma回复了一个害羞的表情。
曲直加快了步伐,把手机装入口袋,心里似乎有点自信了。
不远处,有个小院落,透过竹篱笆墙,有一条小径,杂石铺就,弯弯曲曲,通向餐厅。
曲直掏出手机看时间,见有一条微信,Emma发来文字:
“对不起、对不起,刚才,我给餐厅打电话订座,没想到,他们放假了。您要是愿意的话,来我家吧。不过,我的手艺不太好,也来不及采购了。您来吗?”
哦?邀请我去家里,她家还有其他人吗?曲直心中忐忑,犹豫着,打字询问:
“您住哪儿?”
“黑松白鹿身后,世芳美庭A座2003。”
抬头看,世芳美庭的大牌子就在眼前。
***
世芳美庭距离使馆区很近,大门前有外国人出入,一层是底商,有房屋中介、便利店、酒廊、花店等。
曲直进入花店,精心挑选,买了一大捧郁金香,这才步入大厅。
进入电梯,身后跑来一个七、八岁的白人小姑娘,见曲直按下了20层按键,便缩回手。
“Hi,”小姑娘笑了,操着一口流利的中文,“我猜,您是Emma的朋友。”
“是。”
“我也是。”
“嗯?”曲直心生疑惑,“你怎么知道我来找Emma?”
“很简单,每一层只有两家人,您不可能是来我家,”小姑娘看着花儿,“您在追她,对吗?”
曲直笑而不答。
“Emma刚搬来,你为什么不多陪陪她?她很孤单,除了我,她就再也没有朋友了,”小姑娘望着郁金香,“你很会选花儿,郁金香比玫瑰好,玫瑰很俗气,送玫瑰的人都很俗气。我喜欢郁金香,Emma也肯定喜欢,相信我。”
到达二十层,电梯门开了。
二人出来,曲直抽出一支郁金香,送给小姑娘。
“谢谢!”小姑娘接过花儿,“我叫莉莉,L-i-l-y,您呢?”
“我叫曲直。”
Emma家门开了,她站在门内。
“Hi,Emma,”小姑娘神态严肃,上下打量一番Emma,一手摇晃着花儿,一手掏出钥匙,打开对面房门,临关门,又转回身,对Emma说道,“看来,您今天心情很好。Bye!”
室内温度很高,仿若初夏。
Emma身穿黑色套裙,五官夭丽,头盘高髻,白瓷般的脖颈托着圆润脸庞。面对曲直,手脚踧踖无措,仍是那种略显神经质的神态。
墙角有空花瓶,曲直走去,将花束插入。
Emma脸儿突然红了。这几乎是在明示,我清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且,我做好准备了。
“差不多了,”Emma指着餐桌,转身走向厨房,“你坐吧,随便看看也行。”
房间豪阔,四室两厅,装修为新古典主义风格,家具有使用过的痕迹。曲直随意走了走,站到落地窗前,城市尽收眼底,街道车稀人少,灯火明亮,更显寂寥。
这房子足有三百平米,一个女人住,太空旷了。
“去洗手,”Emma从厨房出来,布设餐盘,“可以吃了。”
曲直洗完回来,餐桌上摆着果盘、蔬菜沙拉、煎牛排、奶油蘑菇汤、冷切火腿。
“时间来不及了,冰箱里有的,我就全都拿出来了,”Emma端来一瓶威士忌,“刚从楼下买的。”
曲直接过酒,酒标写着Starward Whisky,产地是澳大利亚,打开后,Emma将自己酒杯推过来。
碰杯略饮,气氛仍很尴尬。
“你一个人住?”曲直不懂威士忌,不便评价,看着客厅,竟然和自己家一般大小,心生惭愧,话一出口,又想起,二人曾在微信中约定,不问彼此生活,见Emma又举杯,便赶忙岔开话题,“这酒43度,要不然,你喝红酒或者啤酒?”
Emma将空杯推过来。
曲直看着那手,大着胆子,握紧它。
Emma略一后缩,力气小得就像猫咪的反抗,光润白腻的脸上渗出一片晕红,仿佛白玉上抹了一层胭脂,手任由曲直握着,换手端杯,再抿一口。
夜更暗了,风在低声恳求玻璃窗,它想要钻进去,近距离地窥视这对暧昧的男女。
“你在北京过年?”
“嗯。”
Emma缩回手,两手相互捏紧,她自顾自连续喝了几杯酒,神态更加不安。
二人不说话,只是频频举杯。
曲直几乎断定,Emma的情感生活出现了问题,甚至可能是刚离婚。Emma主动将手送过来,曲直接住,触手绵软,却其寒似冰。
雪很大,落得急,北京很多年没这么下雪了。
卧室开着床头灯。
Emma身体裹在被子里,曲直将被子轻轻拉开。
细看,那裸体凹凸分明,艳艳生辉,皮肤很白,仿佛能被灯泡晒黑,又仿佛划破它,流出的是牛奶。Emma伸开手臂,挽住曲直脖子,将他拉向自己。曲直情欲高涨,如同烈焰排空,紧拥下去,深吻轻抚,Emma 遍体潮润,香舌挑送过来。
她伸手将灯关了。
“开灯。”
“不,不行,不开灯。”
“想看着你。”
“不,别开灯。吻我,轻点,轻点对我。”
Emma似乎比男人更了解男人,曲直欲向左,她已在左边等待,欲向前,她早已迎上来。
醒来时,已是凌晨。
曲直翻身起来,Emma不在身边。卧室外,隐约传来说话声,曲直赶紧下地,踮着脚尖,轻轻将门拉开一道缝,隔壁房间亮着台灯,Emma在打电话。
“咱们互不相干,别再给我打电话了,”Emma悄声说话,拿笔纸,记下文字,“明天就给你。”
曲直关上门。
不久,卫生间传来淋浴声。
曲直穿好衣服,进入隔壁房间,纸上写着沈阳生的名字以及银行卡号。
***
快到小区大门时,曲直喊停出租车。
下车后,缓慢走着。
回家后,怎么面对妻子?对于刚发生过那一幕,是后悔了吗?如果后悔,为什么临别时恋恋不舍。如果不后悔,为什么又着急回家?今后,该和Emma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一夜情,或者长期情人?我会因为Emma而离开于薏薏和女儿吗?不,不会,这绝对不会。
打开房门,于薏薏已经熟睡。
曲直溜进卫生间,脱下衣服,扔进洗衣机,开始洗浴。
于薏薏是在装睡,听到卫生间响动,翻身急起,拿起曲直手机,密码已经更换,三试两试,仍是错误。放下手机,恼怒爬上了肩膀、脖子,开始勒紧额头,心越快越快,仿佛到了嗓子眼里。
黑暗中,于薏薏依旧躺下,闭上了眼睛,心里恨曲直,却又不知该怎么办,眼里流出溪水似的、冷冷的、大颗大颗的泪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