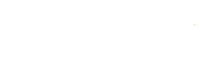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陕西省,好风景,石人石马摆两岭,逛了石马岭,就像逛了陕西省。”上小学的时候,和我们村隔沟相望的石马岭村曾是孩子们的快乐天堂。石马岭上的每匹马都有着我们少年时代的影子和青春美好的憧憬。
石马岭分东岭、西岭、头岭,神道从东岭一直延伸到头岭,石人石马就全部分布在一片片果园里。岁月如一把巨斧把神道劈为两半。一半是东岭,一半是西岭。东岭与西岭之间是一条大沟,沟两侧均有石人石马,遥相呼应,对望而立,这一立就是千百年的光阴。
那些石马,曾是我少年时代最好的坐骑,仿佛一翻身就驰骋在刀光剑影的大唐战场上,挥洒和绽放生命最初的激情,一次次越过古老的时空之门,挥舞着刀枪剑戟。那些石像生曾是我幼小心灵里最初的英雄的光辉形象。在我们村通往石马岭村的每一条羊肠小道上,都曾拴着我的童年。撵牛坡、窨子沟、代家沟……那些熟的透堂发亮的名字里浸满我汗涔涔的思念,那是我生命最初灵魂的地址。那消逝在悬崖边的姑娘,何曾知道一个少年的懵懂心事?沟壑纵横的渭北荒塬,时时牵绕着我追古的心,哪一条是英雄的马蹄所踩踏,哪一条能通往白云深处的人家?
每一次回眸,都是历史轮盘上最美丽的风景线。每一根线条,都是山村时光里最质朴的咏叹调。每一尊雕刻,都是光阴中凝固的音乐,无声无息地演奏着千古不更的守候。我仿佛又回到了烽火四起,动荡不安的唐朝。每当我驻足文官下轿,武将下马的神道上,一颗怀古之心,常常漫成挥之不去的思绪。望着直插蓝天的华表,我常常感到人在历史的洪流中的渺小,唯有这些高大丰腴,栩栩如生的石人石马石狮石鸟们把我领回1000多年前的唐朝。儿时,我和伙伴们把那华表叫通天柱,在我幼小的认知里,我视之如神物,不敢靠近。它不同于西方的罗马柱,上面刻有卷涡纹、龙风云纹,基座上覆莲绽开,顶上仰莲微笑,一只石球极尽古今八荒。
我们村上一家王姓人家早年迁到石马岭村,其后人王申敏从小生于斯长于斯。60多年前,他还是个不谙人事的年纪13岁的懵懂少年。唐建陵墓碑就是从山底下的胡都村(现在昭陵社区街道所在地)用老牛车拉上去的,砌墓碑的砖石是他和村上一帮子少年一块一块背上去的。
话说礼泉县政府曾拨专款对陵前地面遗存石仪进行整修加固,同时为清立陵碑修了砖碑楼。陵碑在献殿遗址中心偏北边,碑高2.68米,宽0.9米,正面竖书三行楷书:“赐进士及第兵部侍郎兼副都御史陕西巡抚毕沅敬立”“唐肃宗建陵”,“大清乾隆岁次丙申(1776)孟秋”。碑背下镶嵌小石碑,记述修复建陵石刻情况,落款:“1957年12月3日礼泉县人民委员会立。”
然而,这一块乾隆时期竖起的陵碑,究竟可以诱惑多少世人探寻大唐的一段历史的真实?一代代守陵人走了,留下一条条通往岭顶的荒芜不堪的神秘之路。陕西巡按使毕沅亲书之碑让人想起一段段古老的故事。虽然隔沟相望的石人石马千年屹立不倒,但在历代被人为破坏现象也非常严重。印象最深的是一些石人石马身上箍的铁箍。月饼大的螺丝锈迹斑斑,一搭眼,就让人不禁感叹,这一个个石人石马在千年人间沧桑巨变中,到底经历了多少磨难和风雨的洗礼?到底站了多久?随后在战乱中倒下,在盛世太平中站起。
西望乾陵,武则天的双乳峰挺拔突兀,一颗梁山主峰做的头颅高昂不屈。东望昭陵,李世民的昭陵直插云天,云蒸霞蔚,虽不见栈道离宫,但气势逼人,恢宏犹在。建陵如一个迎天躺倒的男人,一山一梁一沟两道岭构成一个男人的雄健身躯。虽然历史上建陵之主李亨一生的政治建树不多,晚年凄凉,但一场安史之乱让人记住了这位大唐的皇帝,记住了平定安史之乱的中兴名将郭子仪。一匹匹石马迎着猎猎朔风,威风凛凛,昂首挺胸,一个个文官武臣迎着炎炎烈日,肃穆寂寂,千年不屈。仿佛时刻都在诉说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悲伤,草莽不掩煌煌青史,粗砺不藏鬼斧神工,让人无限神往。
小时候,父亲没给我少讲过关于唐朝的传说。据说,历代的盗墓贼们对昭陵建陵里埋的宝贝一直虎视眈眈。
有一年,石马岭村来了几个盗墓贼。他们日夜兼程,从很远的地方聚集到这儿,趁着黑夜去盗墓,可是,屡盗屡败。每当他们准备挖墓时,黑暗中涌出一群人马来,吓得他们屁滚尿流。后来,他们就花大价钱请了一个道人指点。如果晚上再遇到他们,就藏在暗处,把领头的马先用绳打套绊倒,砍掉蹄子。听到鸡叫,石人石马就不会再动了。
盗墓贼按照道人的指点,夜里突然袭击这些巡逻的石人石马,同时一个个学起鸡叫,四处村子的鸡都叫起来了。这些倒霉的石人石马,搞错了日夜交替的时间,还没来得急赶回原地,糊里糊涂就显了原形,因此,有的倒在地上,摔坏了身子,弄断了腿永远不会动了,就永远撂在了这荒坡野地里。不说远的,1957年那次倒下的石人石马被再次扶起来是真的。也许是因为盗墓贼光临过。
石马岭村的建陵,是唐朝第七个皇帝李亨的陵墓,神道两边石刻作品是风靡千古,精美绝伦。小时候,我常常和战军、军营、小军、军阳等小伙伴们常常一撂下饭碗,就翻沟越岭骑石马去了,惹的父母隔三差五惹的用笤子疙瘩追着我打。而我也常常在石人石马上吃喝拉撒睡,我们爬不上去,就一个先蹲下身,一另一个踩着肩膀爬上去。然后轮流上马,那“驾、驾、驾……”的声音还回荡在空荡荡的沟里,有一次我都差点打盹滚沟了。神道中间历经千年黄土风雨冲刷,沉积为一道苍苍莽莽的百米深的沟渠,沟渠两边土塬上星星点点住着二十几户人家。常常望着九嵕连绵,这些石人石马就活生生跑进记忆深处。
唐建陵有汾阳王郭子仪、皇后张氏、开国公李怀让陪葬墓3座。我的故乡就在唐建陵西南四里处,属陪葬墓区,原有墓冢6座,今仅存4座,分布于村西、村南,两座已无存。坐落在我村上的汾阳王郭子仪墓,已修了祭拜广场,每年清明、国庆前后、农历十月初一都有大量来自美国、加拿大、柬埔寨、泰国、越南、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的郭氏后人,以及省内外同胞来郭子仪墓园祭拜先人。在同一条硷上,距离郭子仪墓东边300米左右的是李亨的皇后张良娣的墓,无碑,二十多年前曾被盗掘过。
张良娣出身官宦世家,祖母窦氏是唐玄宗的母亲昭成皇太后的妹妹,张良娣是窦氏第四子张去逸的女儿,天宝年间入东宫,册封为良娣。张良娣丰满美丽,善解人意,在李亨最失意的时候给予极大的慰藉和支持。后随李亨北上,露营时总在外间,以身保护李亨。灵武产后三天,就亲手给士兵缝衣服。但立为皇后后恃宠生骄,野心日益膨胀、骄横跋扈,被宦首李辅国整天追杀,最终被唐代宗废为庶人,留下千古憾名。我曾经带我的两个孩子去那里玩,穿越一段茂密的小树林和青翠如玉的葡萄园就到了。儿时被盗的张良娣墓南硷下的石门拱顶几乎看不到了。他们兴奋之余,都误以为会会见到一个绝美的大唐美人,看到的却是草莽丛生,野酸枣遍身的残冢疙瘩。而我暗暗地唏嘘不已,不亦快哉!
家乡礼泉县古称寒门,相传乃黄帝升仙的地方。秦汉时称焦获、谷口,南北朝时改为武夷县,隋文帝开皇十八年即公元598年改为醴泉县。唐武德二年废醴泉设好畴县,一年后复称醴泉县,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改为礼泉县,也是一片风水宝地。
唐建陵所在地武将山和石马岭。唐代时,奇花异草遍地,流水潺潺,是皇家冶游狩猎之所。今有御道村、牧鹿村之名始于唐。陵区内有39件石刻。4门各有石狮1对,朱雀门外有石人10对、石马5对、鸵鸟1对、翼马1对、华表(神道柱)1对,玄武门外有石马3对。翼马、鸵鸟、石马、石人一字向北分别相距32米,每对石人南北间距30米,石人身高2.5米,全部隔沟对望。大概八年前建陵东门两只石狮被盗,今陵园内残存石刻有石门狮6只。1957年,礼泉县委书记卓敬云组织人员将每件文物原地扶起,其中一尊华表据说埋没于沟底向南约20米,距地面深约7米的淤泥里。被盗石狮一只张口吐舌,做低吼状,圆目怒睁,鬣毛稀疏。另一只瞋目前视,闭口露牙,鬣毛下垂。胸前刻有“民此远备”,右腿刻有“七月十一起”字样。警方曾经悬赏30万元,至今未果,也成为一件难解之案,实在令人遗憾。
石马岭上的建陵石刻体积较其它唐陵石刻略小,刻工略粗,印证了安史之乱后的唐代经济由盛而衰的状况。但瑕不掩瑜,建陵仍然是中唐时期帝陵的佼佼者,也是是保存最完好的唐代石刻艺术精品。
近年来,经过政府的退耕还林和生态保护,石马岭村绿树遍野,松柏长青,婆娑郁郁。西边沟梁上建立了文管所,有的石人石马旁边安了监控设备,修了柏油路。看着满沟的噌噌长高的的柏树,不禁发出长长慨叹:满沟的活着的兵,没有一个听我命令的。有时候,我曾也自负地说过,我是摸着唐朝人笏板和刀剑长大的一点不为过。因为小时候我的个头只够着摸摸那些文官武将的那些玩意儿,就好像在摸摸千年不变的唐诗,摸着唐朝长长的尾巴。小时候我经常在这些石人石马中追打,骑马威风一把的岁月却不复存在了。
夜雨骑马江湖,一人两袖清风。
松门烛影思量,知交漫客相逢。
那些弯弯曲曲的山道,把一个王朝最值得追忆的一段辉煌藏在草莽荒芜之间,把两座帝王陵的光芒隐匿在纵横苍凉的沟壑皱褶里。那些陷入泥土里的石望柱,安了支架的鸵鸟,嘴被打掉的石马,掉了脑袋的石人,怒目凝视的石狮……常常夜里钻入我的梦乡。我也偶尔登上乾陵之巅,那白云深处,是我永远依恋的故乡么?
人在历史面前,不过是天地之间匆匆的过客,刹那须臾而已。人在神面前,不过是一个个虔诚的膜拜者,一缕香火而已。而唯有石马岭上的石人石马还傻傻地检阅着苍生沉浮和千秋兴衰,但也与天地永恒了。
【作者简介】杨辉峰,陕西散文学会会员。作品散见于报刊杂志。著有散文集《我的村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