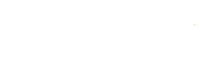中年男人辉哥。
拖着病腿俯视整个香港时,
他看到了不属于他们的灯火通明。
在口琴少年的协助下,
他们一起坐吊车登上深水埗,
正在修建的最高楼。
然后对着下面的万丈繁华,
尿出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好世界。
恶趣味,但够爽快。
繁华,当然不是他们的。
香港,好像也不是他们的了。
他们是住在深水埗的露宿者。
深水埗。
香港出了名的贫民区。
近些年来也迎来了几近暴烈地推倒和重建。
用辉哥的话说就是——
「为什么要来搞穷人的地方,为什么」
比起奥斯卡影片《无依之地》里,
候鸟般的迁徙。
深水埗穷人们更像是终日城市里的浊水一滩。
他们一生都在守在香港街角。
这是他们唯一的庇护所。
城市是他们的,
也不是他们的。
开头的镜头,皆来自于今年金像奖大热门。
《浊水漂流》。
也是金马奖最佳改编剧本影片,和刚刚结束的First影展的大热门。
温馨提示:本文有部分影片剧透
影片聚焦在香港深水埗的露宿者,
和他们所遭遇的,冷眼与烈火。
吴镇宇饰演的辉哥,贡献了贴切的演技。
导演李骏硕说,
我希望拍出深水埗的风貌,那些密不透风,那些推到和兴建。
这部影片在国外展出时,
有不少国外影评人说,这是导演呈现的不一样的香港。
才不是。
才不是。
导演李骏硕说,
「我有点愕然,我认识的香港,从来都是这个样子。」
01
深水埗的日与夜
深水埗在香港,是甚至比天水围还要穷的地方。
这里一直被称为「香港贫民窟」,
也是这个城市的底层聚集最多的区域。
破旧的唐楼、劏房随处可见。
不止这部片,
《一念无明》中的劏房也在深水埗。
很多在香港长大的孩子,或者来香港旅行的年轻人。
经常会听到一句话——
千万别在晚上一个人来深水埗。
说的不止是因为这里的贫穷。
而是伴随着贫穷一并而来的,
复杂人群和不安定的氛围。
辉哥和他的露宿朋友们,就是在这密不透风的夹缝中,
挣扎求生的人。
这群人。通常有个不成文的习惯。
无论多挣扎,千言万语,约定桥底见。
是的。
桥上是富人们的车水马龙,
桥底就是穷人们的日常起居。
刚出狱的辉哥摇摇晃晃,带着中年的倔强。
他回到熟悉的深水埗露宿。
老朋友们相视无语,先行个行内惯例。
行内惯例是什么?
就是对于出狱的人。
桥底迎接他的就是「来一口」。
「不给他们重新做人的机会。」
所以,有人说这群人活该,
也有人反驳,说这是「何不食肉糜」。
事实上,
他们都是来自岁月里各种被遗忘的人。
越战的难民;
出狱后无家可归的浪子;
离家出走的少年;
没有钱住房子的残障人士;
和鳏寡孤独的流浪者。
桥底棚户区人们的生活就像一个小院落。
有人负责电力的接通,
有人负责沟通大小事务,
有人负责搭建和修理棚户。
他们必须互相帮助,
才可以活下去。
这里的「活」,是真的,只是活着。
在深水埗的桥底,落单的人,唯有死路一条。
可除了落单,造成这些无家可归的人的死亡方式有很多。
其中, 有一种方式。
香港食环署称为「洗地」。
就是夜晚突然前往露宿者的棚户区,
清理检查这里有没有违禁物品。
这个夜晚。
食环署没有通知,没有预警。
像台风一样呼啸而来,
把露宿者们的家当一扫而空,当垃圾处理。
露宿者们喊着,
这不是垃圾,这是我们的家当;
这不是垃圾,这是我们的衣服;
这不是垃圾,这是我们用的东西;
无济于事。
食环署连身份证都清理走了。
辉哥和街友们家当尽失。
他们唯有另寻住处。
在另一个桥底搭建小木屋,捡来别人丢弃的钢架床,
相依为命。
收音机、煤油灯、衣服被褥…
重新去筹集。
穷人嘛,生活总是起落落落落落。
好像大家也惯了。
就好像,即便记者来采访。
也对露宿者的诉求并没有兴趣。
他们感兴趣的是什么?
是关于露宿者的悲惨身世和令人同情的流量热点。
辉哥很倔强。
他要状告ZF。
初出茅庐的社工何姑娘足够热忱,
她和街友们一起,
将ZF告上法庭。
辉哥带头,大家一起在ZF门口举横幅——
「露宿无罪,滋扰无理」。
可是无论是公道也好,
还是赔偿也好。
真的能到来吗?
除了赔偿,
辉哥更看重的,是ZF的道歉。
「我要一个道歉。」
寒冬就要来了,
刚刚收留的口琴少年吹起口琴,
辉哥看他就像看儿子,
他说,你能不能不要天天吹得那么惨,
吹一首,欢快一点的吧。
02
道歉与和解
「事已至此,还有什么值得愤怒?」
「那为什么你还要硬撑下去?」
「我干了什么错事?我要讨回一个公道!」
「你不和解就是连累所有人」
「那就揽着一起死吧!」
最终掰头结果。
哦不,根本就不可能不足以有掰头的余地。
ZF赔偿两千元。
大部分人都觉得不错。
毕竟两千元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够生活好一阵子。
但辉哥不同意,「道歉呢?」
何姑娘说,
「他们拒绝道歉。」
「那我不和解。」
辉哥斩钉截铁。
「不道歉,不和解。」
身边的人都开始焦虑,纷纷劝说辉哥。
说如果不接受,说不定接下来连两千元都没有了。
「没有钱,我也要他们一个道歉。」
众人劝说无果。
纷纷离他而去。
前面也说到了,
像这样的露宿者群体,
一旦落单,必死无疑。
何姑娘来看他,
「辉哥你还好吗?」
辉哥说——
「我不和解」。
何姑娘说——
「我啊,也不是来逼你的。」
食环署的洗劫一空如同台风,
深水埗的推倒和重建也如同台风。
新的大楼总要建起。
那么桥底怎么办?
一间一间的拆除吧。
辉哥问过,
你们为什么要来搞穷人的地方?
可能因为,
在高楼上的人,根本看不见桥底。
就像之前有人说,
冬天的冷,是偏心的。
住在楼房里的人,和在户外的人。
过的并不是同一个冬天。
那个晚上。
香港入冬,桥底的穿堂风咆哮而过。
一个不留神。
辉哥居住的那间小棚户有了火光。
他看见了十年前死去的儿子。
「你喝多少,我陪你喝多少啊。」
小屋子熊熊燃烧了起来。
大火旁,车流依然穿行而过,
而大火里,辉哥一直没有出来。
在最后的字幕里,
导演写到:
在之后的一段时间,ZF赔付了露宿者一共两千元。
但至今,都没有道歉。
没错,至今。
而残忍的正是,这部影片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
安得广厦千万间,
ZF共赔两千元。
03
无家可归的人
浮华之下,
香港有的是,无家可归的人。
如果不是夜晚暗自去坐吊车登上那栋未修建好的楼。
辉哥他们永远都看不到整个香港万家灯火的模样。
上楼?
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已。
无家可归的人,视角是平视的,仰视的,远远看着的,
永远都不会是俯视。
2019年,疫情前。
社署能统计到的数据是1270人。
当时,有社区干事称:
「无家者想上楼,只能申请公屋、租私楼或住政府宿舍,但现时“三路不通”,公屋无期,私楼太贵,宿舍宿位不足,加上过渡性房屋多数帮家庭。所以,单身露宿者离上楼,遥遥无期。」
疫情后,
可想而知,状况唯有更甚。
影片里的无家可归之人,
除了辉哥,还有两个人值得一提。
一个,是谢君豪饰演的老爷。
和倔强的辉哥不同,他更温和,更善于打理人心。
在街友们中间,他是统筹者,也是润滑剂。
只是,和本地街友不一样,
他是越南难民。
这里又牵扯到了另一段历史。
上世纪70年代,因为越战的缘故。
很多越南难民涌入香港。
那时候香港是英国殖民地,很多人把香港作为中转站,然后再分去其他地方。
所以,当时建了很多难民营。
老爷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和家人来到的香港。
只是梦碎的是。
当时难民可以等待其他国家收留,故而老爷全家可以去挪威。
但老爷去不了,因为他有案底。
家人和孩子去挪威,他留在香港。
至此杳无音讯。
直到小半个世纪过去。
何姑娘帮老爷在挪威找到了儿子。
老爷隔着视频和儿子相见,
他一生的夙愿,才终于了结。
谢君豪,也贡献了本片最精彩的一段演技。
儿子成器,在挪威成为了建筑师。
老爷问,
「建筑师,那是要给很多很多人盖房子的对不对?」
瞬间泪目。
这个时候,老爷自己能不能「上楼」,已经不重要了。
儿子说,我可以来看你啊。
老爷摆摆手,不不不。
他挥挥手,离开了视频通话。
当晚。
也离开了这个世界。
老爷啊,再也不用上楼了。
另一个。
则是被辉哥当成儿子看待的口琴少年,
也是香港的另一个侧影。
他不穷,甚至还来自香港的高知中产家庭。
可没有人知道,
他为何流浪街头,为何说话不利落,为何带着口琴。
妈妈再见到他时,
询问何姑娘。
他之前是个机灵的孩子,
你知道他是经历了什么变成这样吗?
父母不知道。
何姑娘不知道。
估计,只有他自己,和这个社会知道。
让我们再回到片名。
浊水漂流。
导演把街友们比喻成城市里的浊水,那是一种深深的,逆洪流而上的无力。
他们时而萍聚,时而飘零。
深水涉是属于穷人的地方,
连这里都开始高楼林立,穷人又能睡哪里?
社工何姑娘抬头看着深水埗正在修建的高楼大厦。
她尽管热情,充满善意,但同样无能为力。
社会的问题,只能社会来处理。
就像,她帮助了老爷找到儿子。
老爷不因她死,却因此事而放弃生命。
何姑娘住在自己香港市中心的高楼里,
留着老爷养的那缸金鱼。
金鱼游来游去,游不出鱼缸。
人们也走不出自己的牢笼。
电影上映时,
有人感叹:
躺在文化中心门口的露宿者们,会知道里面正在演关于他们的电影吗?
嗯。
知道又有何用。
不过是两千元啊,至今还没有道歉。
更揪心的是。
就在我敲这篇文章的时候。
香港无家可归的人正在越来越多。
疫情日增最高数字在7000以上,死亡人数也呈上升趋势。
深圳湾通关挤爆。
疫情之下,进不了医院的患者……
怀抱侥幸,偷渡过来的亡命者……
巨大的阴影如同乌云遮罩在这座城市上空。
就像那天晚上,桥底的烈火。
吴镇宇饰演的辉哥在影片中说:
「我不是忧郁,我是愤怒。」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