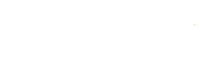张容南 陈子昂 史锦宬 金楚楚 杨小珊
或许每个人都曾思考过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何意义?在疫情隔离的当下,生命的空间被压缩到了方寸之室内,日常生活呈现为不断重复的核酸检测、抗原自检,时间就在三餐之间流走。如果生活是这副模样,那么人生有何意义?若询问人生有何意义,一直以来,答案似乎总是与他人无关的自我思考与自我选择:我可以依据自己的气质和兴趣独立地为自己的人生创造或赋予意义并实现它。在独立性自我的理解下,生活意义来自于制定并自由地追求个人计划。但在疫情的背景下,这种全然的独立性砰然倒塌,我们是如此脆弱,无力独力抵抗这一来势凶猛的病毒,也无法在居家隔离的日子里独立地生活——这种脆弱性也预示着我们是如此深切且紧密地依赖着他人。在疫情的背景下,我们将从哲学-伦理学理论和自己的生活体验出发,一切去探讨一个人生的根本性问题:人生是否有意义?如果有,是什么使得我们的生活有意义?这一段疫情的经历是否会影响我们对于自己人生意义的理解?
2022年5月8日下午三点,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以“何为生活的意义?——疫情蔓延下的生活意义思考”为主题举行“共同抗疫 智性对话”活动。哲学系伦理学教研室的张容南教授与2018级哲学系本科生史锦宬、2019级哲学系本科生陈子昂和2020级伦理学专业硕士研究生金楚楚围绕这一主题展开对谈。
张容南:关于生活意义的思考在哲学史上是一个恒久不衰的话题。疫情蔓延下的隔离生活又提供了一个反思生活意义问题的特殊契机。现代性催生了个体化的生活方式,现代个体容易将自身想象为独立自主的行动者,他们追求不同的生活目标,保障这一套生活计划实现的是个体的权利。但在抗疫的情况下,我们无奈形成了一个个被区隔开的共同体,我们的共同目标是抗疫成功,在此统一的目标下,我们不得不牺牲一些个人目标和行动的自由,服从整体的安排。与此同时,个体的需求凸显出来,我们不得不向他人敞开自身的脆弱性,那种独立自主的自我想象一下子就瓦解了。
隔离生活与正常生活有着非常不同的特点。在正常生活中,我们享有行动和选择的自由;生活具有确定性,即有相对稳定的预期;我们与他人的关系可相对自由地建构;在此条件下,自我容易活在独立自主的想象中。然而隔离生活下这些条件不再具备,我们的行动和选择的自由受限;生活落入不确定性中,缺乏稳定的预期;我们和他人被迫隔离在一起,他人可能携带病毒,我们与他人的关系紧张而微妙,自我因而容易陷入不安与焦虑的情绪中。
这使得我们行动的理由和生活意义的来源发生了一些改变。生活意义是为我们的行动提供基本理由的东西。我们行动的理由一般有两个来源:一是追求个人计划的实现,二是与他人建立或维系重要的关系。这两个理由背后预设的自我理解有一点不同,前者预设了一个有边界的权利主体,后者预设的是一个向他人开放的脆弱的主体。由于疫情期间的行动受限,追求个人计划的实现变得难以实现,但意外地提供了一些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机会。我自己在疫情期间就切身感受到了邻里之间互帮互助的温暖,尽管疫情削弱了前一种行动的理由,却使昔日里疏远的邻里关系得以拉近,以物易物、公益团购、志愿配送、帮助孤老和孕妇配药和就诊;我们基于暂时的共同目标去行动,这些目标的达成给所有人都带来了情感上的宝贵联结。
我们总说“生活意义”,问题在于何谓“意义”。“意义”既不完全等同于“行动的理由”,也不同于“幸福”或“正当”;我们可以说一个小孩是幸福的,却很难将其生活看作是有意义的。意义代表某种反思性的成就,它不是全有或全无,而有程度之分。例如,生命的某些时期比其他时期更有意义,而某些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比其他生命更意义。一些观点认为,生命意义的概念是多元概念的集群或混合,如实现更高层次的目的,获得大量的尊重或钦佩,具有显著的影响,超越一个人的动物本性,或展示一个引人注目的生活故事。另一些观点则认为,生活意义主要是一元论的,例如,专注于更高级的善(Taylor)、超越自己的极限(Levy)、或为人类做出贡献(Martela)。
那么,我们可以进一步看看哲学史上三种主要的、对于生活意义的回答,分别是由神圣存在赋予意义的超自然主义、关注主观偏好和(或)客观价值的自然主义以及否认生活具有意义的虚无主义。就这三种回答而言,每一个认为生活具有意义的人都需要认真去思考如何回应虚无主义带来的挑战,而我们普通人一般都会从自然主义这一进路来理解生活意义。所以,我们来着重探讨“自然主义”的三种进路:
第一种是以哈里·法兰克福(Harry Frankfurt)为代表的主观主义,这种观点认为只要一个人做了他认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或者,只要一个人关心或关爱某物,他的生活就是有意义的。这种对生活意义的理解容易陷入琐碎、主观化的风险。
第二种是客观主义——如果我们有意识地花费生命来生产对自己或他人有价值的东西,那么这样的生命就有意义(Ingmar Persson&Julian Savulescu)。这一立场是主观主义的对立面,其问题在于,如何来确定什么是客观上有价值的东西?将客观价值视为生活的关键追求可能会绑架“我”的生活,让他人决定“我”的生活是否有意义而非由我作主。
第三种混合理论糅合了上述两种观点的立场,即当主观吸引力满足客观吸引力时,意义就产生了。也就是说,只有真正地认同并关心那些客观价值时,它们才能成为我们生活意义的来源(Susan Wolf)。这一观点看似比较合理,但也有其问题:倘若能由自己选择作为生活意义源泉的客观价值,这种选择的限度有多大?混合理论有滑向客观主义的风险。
基于上述关于“生活意义”理论思考的一般性介绍,不同的同学可能对疫情背景下的生活意义有不同的思考。那么,疫情是否会带来对意义的消解,如同严重的疾病对一个人的伤害那样,瓦解我们的意义世界?带来虚无主义?疫情下的反复检测、生活场景的单调,容易使我们的时间感变弱,平日和周末没有区分,每天都是一样的,令人容易产生重复感和无聊。就像电影《土拨鼠之日》的男主角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生活,这样的重复容易损伤生活的意义——生活停止更新,我们无法体验到那种生命有高有低带来的节奏感,尤其是难以体验到满足感(feelings offulfillment),例如我们去打一场篮球回来所拥有的满足感、做了一个获得老师和同学一致夸奖的报告等。与之相反,每天不断重复的生活会带来一种无聊感(feelings ofboredom),日子感觉看不到头。还有,疫情之下的不确定性就像一个黑幕,带给我们不安和恐惧,这种不确定使我们的生活压缩到最基本的层次——如只求基本的一日三餐,无法去设想更高层次的自我实现,严重压缩了生活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所以,这种不确定性也是对我们生活意义的打击。或者,疫情是否会破坏我们真正关心的事物,加重我们的无力感,能动性受损,从而削减我们生活的主观意义?比如说,有同学一直很关心楼下的流浪猫狗,但由于现在疫情隔离,自己都无法照料好的情况下他可能也难以去保护那些小猫小狗,这时候自然也会产生无力感。又或者,疫情是否降低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从而破坏我生活的客观意义呢?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能力受到限制,我容易陷入沮丧,也很难去提升自己或去服务于他人。由于每个人的性格特质和生活体验的不同,不同的人对于上述的问题可能会有不同的思考和回答,但我可以提供一个看待这些问题的可能视角:如果生活意义是一个人对他生命的整体意义的感受,可以预想总有一天隔离会结束,我们每个人都将回到正常的生活之中,那么这段特殊经历的“走低”,却可能让我今后的生活体验“走高”。例如,饥饿让我反思食物的意义,当我以后吃到不喜欢吃的菜时或许会想到这个菜也是来之不易的。我听到一个朋友说,疫情下的隔离生活正好是一个教育孩子的好时机,因为他们从小生活在衣食富足的环境里,从来不知道什么是匮乏、什么是欠缺,但现在他们知道了。因此,从叙事的角度来看,疫情当下的“走低”和以后有可能的“走高”,也许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个正面的激励。
虽然我们现在还处于隔离阶段,但总有一天它会结束;当以后我们远离这段经验并对此进行反思时,我们肯定会追问这一段人生经历对于我的人生整体而言意味着什么?在我的生活故事中,它占据什么样的地位或角色?对此,我们或许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向来思考:就疫情带来的消极影响而言,它是否影响了我人生计划的实现?我的个体能动性是否受到了损害?就疫情带来的积极影响而言,它是否拉近了我与他人的关系?塑造了一个友爱的共同体?更值得思考的是,疫情这段经历对我们人生意义的影响是否是永久的,我们对自我、人生以及生活价值的理解是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陈子昂:老师刚刚也提到了我们现代社会中自由主义叙事的吸引力,也提到了疫情这样的状态带来的对于自由主义叙事的反思。我们不难发现权利退居了二线,而人的脆弱性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自由主义的个人观念的确存在着诸多问题,其所要求的自主选择与为自身选择负责并没有提供任何关于何为一种好的生活的指导与帮助,其实自由主义的叙事的确让个体格外的脆弱。但与之分庭抗礼的应该是一种在正常情况下行使的,社群主义下的共同体,而非例外状态下的一些所谓团结互助。且不说这次的疫情是否真的让邻里关系变得团结互助,我并不否认在这个城市的很多地方人们完成了很多很有爱的互助行为,可能我看到的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基本的生存需求而发起的一些基础的交换行为。但我想表达的是,在一个对于未来连有限的期待与计划都难以做出的状态下,我们并没有理由希望产生一些甚至能够提供生活意义的共同体。
在例外状态下谈论生活的意义我个人认为是一件比较奢侈的事情,无论这个生活意义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若对生活的意义持有客观主义的立场,那么类似于客观清单理论(objective list theories)中所列举的大部分获得生活意义的要素,在如今的情况下都是无法被满足的。当然,这里要求客观清单的制定仍然是能够被大多数个体所认可的,而非一种强制的好生活概念的灌输。正如老师刚刚提到的,幸福与意义是应该被区分开来的概念,一些低阶的欲望得到满足并不能够在意义中占据很重要的位置。而自由,幸福以及创造性活动是现今时代能够被普遍认可的,好的生活的必要要素。在疫情封控的条件下,我们没有资格讨论“客观清单理论”所面对的类似于通约性和入选标准等理论内部的张力。因为人们被限制了行动的自由,这令他们对任何有意义生活的追求都变得困难重重。
若转向主观主义的立场,封闭更是对于生活意义的摧毁。对于偏好主义来说,其要求事情按照主体的期望进行发生,从而对于主体偏好进行满足。对于Thomas Scanlon的目标成就主义来说,个体也丧失了实现自身目标的许多方式和途径,以至于对于人生意义实现的失败。封闭期间讨论主观主义的好生活的实现,我个人认为是一个不恰当的,过于严苛的标准。对于很多为自身病痛得不到及时救治,为基本温饱需求而困扰的失去自由而无能为力的挣扎个体来说,他们的生活已经和自身的偏好,以及生活的意义脱钩了。
我无意去重复大家所经历的艰难,我只是想强调对于矮化了的个体来说,我们在这一特殊情况下所面临的问题其实并不是该如何积极地实现自身生活意义的问题,而是如何避免生活意义丧失的问题。我们没有理由期待在疫情之后能够形成更团结,更具有共同价值的共同体。人们增长了对于随时可能会失去的实现自身生活意义的担忧(甚至生存),以至于随时要为不确定的生活做好充足的准备。这类不安定的状态只会将个体割裂开来,专注于保障自身的生活和生存(不难发现在封控期间,很多人不惧惩罚,从倒卖物资当中尽快的获取利益)。疫情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对人们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不但降低了生活的质量,更是破坏了每个人所关心的事物。
我个人认为疫情并不存在一些对于生命整体和未来的积极影响,美化一些苦难只是推卸了个体本应该承担的道德判断的责任。疫情以及现在的应对措施的确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计划,甚至是很多个体生存下去的机会(很多人要面临失业、穷困等现实的生存问题)。其也并不会构建起友爱的共同体。也许这样的生活终究是暂时的,但是永久性的影响已经造成,个体心态的改变也已然发生。但我认为其并不是让个体重新审视了对于生活来说真正重要的事情,而是让人们明白也许很多习以为常的价值是如此的重要与不可失去。悲观地说,人们的心态将从去追求更高层次的生活意义(也就是属于自己的,多元化的生活意义),转向尽可能保护住最低层次的生活意义以及作为个体的个人权利。
张容南:谢谢子昂同学!他的发言和思考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反思。总体来讲,子昂同学的思考是相对悲观的,因为他觉得任何积极实现生活意义的可能性在当下是不存在的,更急需的是我们如何去保住一些最基本的东西,避免陷入意义的虚无之中。而且,他还提到疫情并不能让我们收获一个更友爱的共同体,而是愈发地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脆弱性,然后持续地为不确定性做好准备。关于不确定性这一点我有类似的体会,就像在疫情之前,我们无法理解老一辈人囤食物的热情,但经历这一次疫情之后,很多年轻人都开始囤食物了。比如说,现在形势逐渐好转了,我们小区团购食物也相对容易了,但是每次团购大家还是疯狂地买,生怕哪天又买不到了。这就是疫情留下的心态模式。
史锦宬:生活意义的提问有两种方式,主观方式和客观方式。主观方式即我们从自己的角度追问自己的生活是否是有意义的;客观方式则是从第三人称的角度去评价他人的生活方式是否是有意义的。我认为不应当把这两种方式混同起来,当我们以客观的方式评价他人的生活的时候,我们是在对他人的生活质量做出价值判断;当我们以主观的方式追问自己的生活时,我们并不想得到一个客观的价值判断。我们在以一种内在的角度确认自己的生活是否值得过,换言之,我们在体验自己的生活,我们在面对自己最本真的时刻。疫情之下对生活意义的追寻,首先是在主观方式上击中我们的。这是第一个层次。第二个层次,在主观方式的追问之下,生活意义的问题也展开为两个维度。以赛亚·伯林曾把自由区分为两个维度,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一种边界的,底线的自由;积极自由是自主的,实现的自由,同样的,生活意义也可以区分为消极意义和积极意义。积极意义是个体性的意义,他和每个人独特的生活历史有关。消极意义是意义的边界,是产生意义,阻止我们自我毁灭的底线。这种意义被我概括为必须活下去的理由。加缪曾经追问过这个问题,他说自杀是唯一严肃的哲学问题。疫情之下的现实,世界展露的面孔,冲击到的是根本的消极意义。世界的荒诞构成对人的生活的否定。但是这是否意味着一种虚无主义?按照加缪的讲法,或许是的。但虚无主义会走向一种积极的斗争的生活姿态。加缪教导我们,不应当消除荒诞,而应当承认它。当我们意识到希望是一种自我欺骗,世界会不断对人露出敌意,生命和世界被放在荒诞的两端的时候,幸存就是一种斗争和幸福。我觉得这是至今仍有借鉴意义的地方。
张容南:锦宬同学从虚无主义这一视角去反思生活意义,非常有启发性。与陈子昂同学不同,他认为疫情恰恰提供了一个反思生活的契机。它让我们意识到平时习以为常的生活原来并不那么习以为常,它是在很多有利的条件以及充分的保障之下我们才能够获得的。而疫情恰恰把这些有利的条件都摧毁了,从而使我们的生活压缩到维持存活。荒诞正是稳定性预期的瓦解,我们把我们的欲望投射到外部世界,我们通过行动来实现我们的目标,这些前提构成了我们生活不荒诞的前提。但疫情打破了这些前提,因为我们只能拥有希望——但希望本身是不确定的,可能会实现,也可能不会实现。所以,疫情破坏了我们常态生活下对生活意义的寻求。
金楚楚:其实我思考更多的是个人和社区之间的关系。首先,个人和社区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就是疫情的感染范围——一个人确诊新冠,整栋楼和整个小区都会受影响,因此一栋楼会集体做核酸,邻居彼此之间会互相提醒注意安全,甚至会发生争吵,比如一个人要去取快递,另一个人会说收快递有可能会附着病毒,你能不能为别人着想。其次就是团购,我把它看作一种更自治的自救方式。我们小区体量比较大,因此团购的团长也多,初期开的团其实是很混乱的,我们买过一个蔬菜包,一半菜都是烂的,但是去找团长,他也没有提供任何售后,退了我们五块钱。中期就是开了很多不同的团,演变出了两种,一种是公益零利团,一种是团长会收手续费的团,前者一直运行到了现在,群里环境很好,如果有独居老人,团长还会免费给送物资,在公益团的群里,只要是和疫情前价格一样的、经过居委报批的团都可以在这里发,各个团长之间关系很好。我自己觉得团长很厉害,尤其是长时间地持续地运营团购的团长。在我看来,团长和自愿者以及团购者之间其实形成了一个小的自治组织,而且团长和志愿者其实是真的以一种帮助、服务的姿态来和大家沟通的,因为我们在生活中绝大多数接触的都是自上而下的管理式的姿态,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生活中的改变。当然,期间会产生各种矛盾,团长也会承担很大的压力。同样也有管理式的团长。这种社区团购的自治模式还处在一种探索的阶段。当然更延伸的联系其实就是传统意义上的邻里关系:相互帮助,物物互换,及时沟通最近的团购信息,甚至是见面打招呼交流近况,这在一定程度上是营造出了一个具有友爱这种特质的共同体。最后我想说的是,一个正常运行的城市应该是不需要依靠“附近”的,因为它具备足够的基础设施来满足每个独立人的需求,让其能够自给自足,我们能够有各种自由的选择,选择自己所认为的好生活,不能够因为这种非常态而遗忘常态的城市管理。
张容南:楚楚同学分享了她在小区隔离期间的经验,包括了邻里间的互助,我们与他人关系的改善,社区自治的探索。疫情结束后,我们不再会在受限的情况下满足生活需求;但疫情确实充分暴露了我们的脆弱性,我们与他人不得不相互依赖。如何保护人的脆弱性应成为公共卫生伦理考虑的一种重要价值。Cheshire Calhoun认为,有意义的生活意味着将你的生命时间花在根据你的最佳判断,你有理由珍惜并因此有理由利用自己时间的目标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目标是值得我们花费时间的?如果我们将自我利益视作生命意义的主要来源,那么,死亡将立刻摧毁我们的生命意义。唯一让死亡并非毫无意义的途径,就是把自己视为某种更大的事物的一部分:家庭、社会、国家……如果我们的行动有超越自我利益的关注,那么死亡就无法摧毁我们对更大事物所做出的累积性的贡献。所以,在疫情这种特殊的生活状态下,关注和爱护身边具体的人、多确立一些超越自身利益的追求、多建立一些有益的联结或许是一些思考人生意义的有益方式。
附张容南老师给的参考阅读书目
吕克·费西,《什么是好生活》
Belliotti, R., 2019, Is Human Life Absurd? A Philosophical Inquiry into Finitude, Value, and Meaning.
Leiden: Brill.Belshaw, C., 2021, The Value and Meaning of Life, London: Routledge.
Benatar, D., 2006, Better Never to Have Been: The Harm of Coming into Existen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alhoun, C., 2018, Doing Valuable Time: The Present, the Future, and Meaningful Living,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ischer, J. M., 2009, Our Stories: Essays on Life, Death, and Free Wi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rankfurt, H., 1988, The Importance of What We Care About,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The Reasons of Lov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有中译本)
Goldman, A., 2018, Life’s Values: Pleasure, Happiness, Well-Being, and Mean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az, J., 2001, Value, Respect, and Attachmen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有中译本)
Scheffler, S., 2013,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2020, Why worry about future generation, OUP.
Williams, B., 1973, Problems of the Self,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The Meaning of Life:A Reader,2007, Klemke, E. D. (EDT)/ Cahn, Steven M. (ED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f, S., Meaning in Life and Why It Matters, 2010,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责任编辑:黄晓峰
校对:丁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