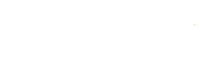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杨辉麟/散文
早饭后,我们离开了林芝波密县的扎木镇,沿帕隆藏布江向西挺进。一路林木葱茏,怪石嶙峋,中午便到了被称为“百慕大魔鬼三角区”的通麦。通麦在一条山洼里,海拔只有一千八百多米。这里群山迭翠,古木参天,溪流淙淙,烟雾茫茫,别有一番深邃恬静的诗意。
这里,只要有土地的地方都长满了绿草,十几株玫瑰,挺立着两米多高的枝杆,缀满了红艳艳的花朵,令人喜悦和赞叹。
据说,孟加拉湾的暖湿气流扑到这里,被山峦所阻挡,常常倾泄而下。充沛的雨水使这里草木繁茂也带来生态的破坏和自然的灾难。这就是过量的雨水造成堆积层地带山体塌方、滑坡和泥石流。我们在距通麦八九公里处就见到半面山体刚倒塌下来,两人全抱不过来的大树也根朝上倒栽在帕隆藏布江里。
晚上,我们住宿通麦兵站。听兵站的小张讲,通麦的烟云婀娜多姿,柔媚动人……
次日早饭后,我们步出兵站,只见四周山峰上轻烟缭绕云团锦簇;苍山碧水,全为云妆雾裹似烟似雾,隐隐绰绰一派诗情画意。
特别是那变幻莫测的云海和山雾,更使人眼花缭乱:一会儿晴空如洗万里无云,蓝天与白云交相辉映,远山与近壑层次分明;一会儿山风呼啸彤云翻滚,恰似江涛横溢江水漫流;一会儿浓雾弥茫遮天蔽日,简真分不清哪是水哪是雾哪是云。只听得山涧泉水潺潺,树上百鸟低唱……
瞧,这里的云雾似乎一直在动一真在变:忽而似轻烟忽而如薄雾,忽而像棉絮忽而同瀑布,忽而若沉睡的雪山忽而像辽阔的海洋……有时聚合有时分离,有时角逐有时蹒跚……
瞬时微波荡漾流水缓缓,瞬时浊浪排空惊涛拍岸……那变化无常的奇妙,实在使人目不暇接。对面明明是万丈深谷,云雾的帷幕拉过来深谷立刻铺平了;左右明明是险峻的高山,云雾的纱帐扯下来高山马上消逝了……
这里,天和地连成一片,云和山拥抱在一起,雾去云来,气象万千。云、雾、山、树……迷离恍惚千变万化。忽然,雪峰从云端出现了,仿佛是天上繁华的宫殿;山峦在雾霭中复原了,宛如大海中美丽的群岛。然后,消失、出现,又消失、又出现,再消失、再出现……山高、云浓、雾深,给人一种“天低云近”的感觉。
通麦烟云之美,和通麦日出之瑰丽是分不开的。凌晨,只见那云海茫茫的天际,在那奇峰突起的山间,慢悠悠地升起了一片绚丽灿烂的朝霞。顷刻之间,一轮红日喷礴而出,吐出万道金光,把蔚蓝的天空装扮得五彩缤纷。
金黄、橙红、淡紫、浅绯……在阳光的照射下,众树如同肃立的人,依就山势从眼前直至天际,最初我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么浩荡一片竟会如此静寂?静得那么安然那么气度不凡,白云在此也端坐不动。
任何伟大的自然景观,留给人的印象都不会是奇异、喧腾、姿态万千的,它是宽广和巨大,也是朴拙和平实,这些伟物透露出的是一种静穆的气息,这是能征服一切的超凡气质,如巨川如海洋如雪峰……注视着这莽莽森林时,我这样想着。
在这里,随处可见那些劈开的木头段子,摊躺在地上散发着湿润的气味。木头建的房子,木头垒的院墙,木头当柴烧……木头,木头,到处都是木头,这令我觉得既可惜又羡慕,也真切地感受到满足使生活变得殷实的从容。
那年,我偶然参加了一位战土的葬礼。据说是伐柴禾时被倒下的大树压死的。在那座准备出殡的院子里,有一副很大的木棺,全部是用厚木料做成的,一头翘起宛如一艘船,看着这样的装殓物,我觉得一个人的去世,就好像一部大书合上了,被封存起来……
午饭后,我们在一位藏族人家里做客。我们坐在木堆上,听主人普布讲通麦人用木头制成的生活器皿用木材支撑的板屋……听他唱那如风在林间穿行的古老民歌,我能咂摸出通麦人的骨血里,与森林那近似亲缘的联系。普布的亲兄弟坐在屋角晒太阳,说起这个兄弟,主人的妻子央金十分气恼,她恨恨道:“只知喝酒,把一份有工资收入的工作也喝没了。”那个五短三粗的汉子依然木讷地坐着……
告别普布一家,我们来到公路边的一家甜茶馆。甜茶馆虽简陋却生意兴隆,里面烟雾腾腾,那泼辣的藏族老板娘响亮而有力的脏话,令我们一惊一乍。这家甜茶馆还经营青稞酒、点心什么的。我们也要了两瓶啤酒喝着。后来进来一位藏族猎人,背着一支猎枪,约莫40多岁,拎一只大麻袋,在我们身边坐下。我们想与他攀谈,无奈他只是一口口地喝着青稞酒,并不说话……
此时,夕阳映红了雪峰,苍茫的暮色笼罩了群山,蓝莹莹的帕隆藏布缓缓流向雅鲁藏布江,我心中涌起诗情,不由得吟道:啊,通麦,奇异烟云莽莽森林!
∥喜欢的话,请关注@读走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