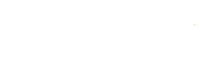这是我家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
记忆里,与父亲第一次见面,是在我号啕大哭中拉开序幕。
“孩子还小,等长大就好了……”在那个明媚的午后,母亲无奈地安慰着父亲。父亲笑着收回了伸向我脸蛋的手,双手局促不安地交织在一起。
也难怪,彼时父亲长年在离家3000多公里外的海岛上服役,一家人聚少离多,能够团圆的日子屈指可数。
记得那是一个下午,父亲带我去市场买了很多玩具,我特别开心。临回家时,我突然冒出了一句:“叔叔,你也早点回家吧!我和妈妈要休息了……”
听到这,父亲红了眼眶。
母亲是一位坚强的女人。父亲长年不在家的日子里,她要照顾我,还要兼顾双方父母,颇为不易。
小时候,我们家条件不太好。为了应对家里开销,她一边带着年幼的我,一边在菜市场卖鸡蛋。冬天的菜市场很冷,母亲在寒风中抱着我吆喝买卖。
年幼的我体弱多病。一次次,母亲带着半夜发烧生病的我奔波在漆黑的夜幕里。那时我无忧无虑,未曾读懂母亲背负的生活重量。
7岁那年,我和母亲随军来到部队。车子在乡间道路上颠簸,深夜时分我们终于到达驻地。
母亲期待多年的团圆梦成为现实,我像被压在五指山下的“孙猴子”,以往在母亲面前的宠溺和娇惯再不敢有所露头。
父亲皮肤黢黑,身材壮硕,脾气急,做事雷厉风行,收拾起我来也如“秋风扫落叶”一般,没有半分懈怠。虽然只有我一个孩子,可他对我要求很严,从不娇生惯养。
我知道,这是我家一直流传下来的传统。自太爷爷走上抗美援朝战场起,一家人就陆续走上了从军路。父亲18岁那年,独自一人背上行囊,告别父母,来到部队。多年的军旅生涯更是塑造了他铁面无私、说一不二的性格。
随军后,一家人看似团聚了,其实父亲常年跟随潜艇出海执行任务,一家人仍是聚少离多。
我们父子俩交流并不多,在我心里面,他更像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即使是多年后我考上军校,遇到什么事总会想到先给母亲打电话。
他是个好兵,却算不上一个好父亲
自打我随军来到部队大院第一天起,我就知道父亲是一个好兵。
为了及时赶上演习,父亲做完手术还没有拆线就咬着牙坚持上战位。
那时家里仍不富裕,身边的战友遇到困难时,父亲总会慷慨解囊,这也引来母亲埋怨他“打肿脸充胖子”。
父亲工作非常敬业,光是日常记录的专业理论笔记就堆了满满一大摞。他从不信奉“教会徒弟,饿死师父”这套理论。战友们遇到难题他总是倾囊相授,为单位培养了一大批业务骨干。
岛上生活很苦,常年酷暑难熬,一到夏季更是风吹石头跑。长大后,我曾问过父亲坚守在这里的意义。他没有长篇大论讲道理,略为沉思后对我说:“以前我们刚来的时候,比这还苦得多咧,现在日子可是好多了。”
在我看来,他是个好兵,却算不上一个好父亲。至少,在我眼里,一个好父亲的定义应该是包容、理解和陪伴,而不是命令、执拗和缺席。
矛盾在我高考结束的那个夏日爆发。
“张南翔,你给我去考军校!”
“当兵有啥好?在那个破岛上,你到底图个啥?”
多年来,接送我上学的是母亲,开家长会的也是母亲,甚至受委屈了也只能找她倾诉。现在,父亲凭什么支配我的人生?
那时的我,正处于“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年纪,更何况从小长在部队大院,早就对军旅生活失去了新鲜感。我们之间的“战争”轰然爆发。
最后,我还是拗不过他,迈进军营的大门,成为我们部队大院里走出的第一名军校生。
收到录取通知书那天,面对大家的祝贺,我心里对父亲竟产生了一丝怨意。
到军校报到那天,父亲特意请了假,并郑重地换上了海军常服。一家人行走在校园的林荫大道上,父亲一级军士长的硬质肩章在阳光映照下熠熠生辉,赢得了无数目光的敬意。战友们说,成为“兵王”是一名士兵至高的荣誉。
送我到学校,父亲在校门口哭得像个孩子
都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而我的思想在入伍之初就抛了锚。跑步跑不动、器械拉不上去、内务卫生一塌糊涂……就这样,“兵王”的儿子被慢慢贴上了“后进”的标签。那段日子里,我常常在深夜辗转反侧,对父亲的抱怨更深了。
从小到大,我在他心里到底是个什么位置?
其实,我一直知道父亲心中有一个军官梦。他的军旅之路颇为坎坷。入伍第3年,他曾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成为一名军校学员。没想到,他文化底子太差,多门考试挂科,被迫退学。回到部队后,父亲不甘心,潜下心钻研业务,并在多项比武中摘金夺银。可是,阴差阳错,他还是和提干失之交臂,最终与军官梦挥手告别。
母亲从不让我在父亲面前提这些往事。可每次想到父亲的这个心结,我对他的抱怨又添了几分:“凭什么要把你的意愿强加在我的身上,我又不是你的兵!”
挂科、违纪……浑浑噩噩成了我身上摆脱不了的常态。
母亲从电话中得知了我的迷茫。那天,我又满腹牢骚地一通抱怨。电话那头,母亲沉默一会后说:“其实,你爸才是最爱你的。那天把你送到学校后,他在校门口哭得像个孩子。”
听到这里,我满是惊愕。在我印象中,父亲是一个“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人”。在长达30年的军旅生涯中,他曾无数次在惊涛骇浪中直面生死。
他居然也会流泪?这是我从没听过的事情。
那年夏天,学校没有放假,我们在营区组织强化训练,父母来队看望我。父亲一改以往的沉默寡言,絮絮叨叨和我聊了很多他的故事。
临走前,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说:“那年你还小,我随潜艇执行任务遇到险情,心里面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现在能看到你顺利长大,我感到很欣慰。”
夕阳的余晖,把父亲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我突然发现,他平日里笔直的身板有些佝偻,两鬓也添了许多白发。原来,在我眼里无所不能的父亲,也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普通人。
母亲说,我奋力奔跑的样子,像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
战友们都说,我真正发生变化是在那个夏天以后。他们发现,我眼神里的迷茫少了,昂扬奋发的斗志足了。
每天晚上熄灯后,健身房和操场跑道上总能看到挥汗如雨的我,学校图书馆也成了我周末“打卡”的宝地。
正当我满怀憧憬奔向未来的时候,一场意外降临了。
助跑、起跳、落地……那天下午,我和往常一样在操课结束后独自加练。飞跃矮墙落地那一瞬间,我清晰听到了自己左膝盖错位的咔嚓声,当时便再也无法站立。
疼痛难忍,可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只是简单的膝盖扭伤,休养一个月后又重新踏上训练场。谁知,在随后的木马训练中,我落地瞬间再次轰然倒地……
父母闻讯从家里赶来。华西医院给出的诊断结果让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左膝前叉韧带断裂、半月板撕裂。这是一场不可逆的严重伤病,如果不做手术将无法剧烈运动。
此时,距离我的毕业考核仅剩一年时间,而手术休养至少需要一年以上。我想起了父亲曾经失之交臂的军官梦,心中不由恐慌。
难道,同样的命运也摆在了我的面前?我怎么能甘心!和父母商量后,我很快就有了自己的打算。
这注定是场一个人的战争。
能下地后,我开始了恢复训练。从每星期完成一个5公里,到每个星期坚持跑完3个10公里,被汗水浸泡出盐碱的护具见证了我的咬牙坚持。上肢力量训练、核心力量训练……几乎每个周末我都泡在健身房里。
距离毕业考核只有3个月时,我们进入深山开始封闭式集训,为考核做最后的冲刺。那时,我仍不确定自己能否顺利通过毕业考核,觉得自己遇到了人生中最迷茫的一段时光。一个个辗转反侧的夜里,父亲反倒成了我最大的精神支柱。
考核的日子如约而至。父亲不远千里来到考核场为我加油。每当我跑完一圈,他便向我挥手致意。最后,我终于咬牙顺利完成了全部考核。
母亲说,我奋力奔跑的样子,像极了父亲年轻的时候。
有一天,我也会成为父亲
得知我毕业后来到遥远的新疆工作,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父亲反倒有些局促不安。
听母亲说,那段时间父亲总是失眠,生怕我到了新单位后不适应。
火车一路驶向新疆。看着映入眼帘的荒漠戈壁,第一次来到北方的我甚至有几分兴奋,一路上不断将沿途的风景拍下来发给父母。
驻地偏远,但人心很暖。到单位后不久,支队首长得知我的伤病情况后,立即安排我去大医院做手术。
接到电话,刚退休的父亲还没有在家享受一天安稳日子,便带着母亲从5000多公里外的家中赶来,在我身边日夜陪护。期间,奶奶身体出现状况,父亲又赶回浙江老家,安排奶奶的手术事宜。
父亲一直觉得自己对家人亏欠太多,也一直在努力为家人做些什么。待我伤愈后,父亲坚持要亲自感谢部队领导和战友,不远千里送我归队。
那是一个下午,父亲提着行李箱步履蹒跚迈入火车,满头银发在阳光下格外醒目。
火车启动的一瞬间,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就像父亲那年送我上学一样,此时我已经换上了崭新的中尉军衔。
现在,我已在基层部队任职近3年。平时在工作上难免遇到困难,每到这时,我总会想着“换成父亲,他将会怎么做”。慢慢地,我好像寻找到了一种攻坚克难的精神动力。
离家久了,我偶尔也会想家,脑海中会浮现出父亲年轻时坚守海岛的画面。我时常在想,多少年以后,有一天,我也会成为父亲,也会生出满头银发。或许,那时我便会真切懂得送我参军、盼我成长的父亲。
上图:张南翔一家三口合影。
图片由作者提供
版式设计:梁 晨
作者:提供
来源: 解放军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