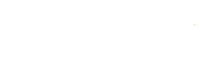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西瓜,甘甜可口的西瓜。”小区北门瓜农的一声吆喝,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记忆之门。
一九八二年夏天,七月到了,暑假开始了。母亲种的西瓜熟了,青圆满地。自家吃不完,送人吧,院子里的叔伯家种的西瓜更多。
母亲就寻思着卖瓜,换两个钱贴补家用。离家最近的宋集是卖瓜的去处,上好的西瓜每斤五分钱。不要小看五分钱,当时鸡蛋五分钱一个,火柴五分钱一盒,油条五分钱一根。
记得有一次,后院大婶家,盐吃完了。对于庄稼人来说,断盐是万万不行的!庄稼人干活需要力气,长期不吃盐,人没力气。
吃过早饭,大婶把家里扒拉了个遍,筹备到九个鸡蛋。可粗盐五角钱一斤,实在没办法,大婶就在鸡窝旁边等。等鸡再下一个蛋,凑成十个。
到半晌午,终于有一只母鸡率先完成了任务。大婶把热乎的鸡蛋装进袋子,匆忙朝集上赶。等赶到集西头,鸡蛋行里空无一人。
大婶只好往家回,可锅里不能没盐啊!“嫂子,你家的盐借点吧?”做中午饭时,大婶端着一只空碗站在我家灶屋门口。母亲用盛饭的勺子从黑色的盐罐中挖出大半勺给她!
叔伯家种的西瓜也卖,他们通常到长官去卖。虽然路途远点,但可以卖个好价钱。据叔伯们讲,一车瓜可以多卖二十多元。更令我心动的,是叔伯们说卖完瓜吃猪蹄。
刚出锅的猪蹄一摸直晃,用嘴一咬,油香入喉。慢慢咀嚼,劲道!叔伯边说边吧嗒着嘴,我听得口水直流。回到家,我就鼓动哥去长官卖西瓜。
“我们也是男子汉,叔伯们能去,我们也能去!”我用小手拍着胸脯保证,能步行走到长官。母亲起初不同意,可经不住我和哥的死缠烂打,只好点头同意。
去长官的头天晚上,夕阳似落非落,母亲从西瓜地里挑出二十三个上好的西瓜。我和哥哥在架车上铺一层厚厚的麦秸,路途遥远,以免赶路颠簸晃坏了西瓜。
我家的架车短小,二十三个西瓜刚好装满。叔伯家的架车长的多,也宽的多,能装三四十个大西瓜。吃过晚饭,母亲让哥和我早些睡下。
第二天一早,天蒙蒙亮,哥就把我从床上拽了起来。母亲已经烙好油馍,冲了两碗鸡蛋汤。吃过早饭,我一抺嘴打了个饱嗝。母亲将装满开水的军式水壶递给我,留路上渴的时候喝。
说起军式水壶,那是我的战利品!军式水壶原本是大伯家的,大伯是退伍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每次到大伯家玩,我总是把军式水壶灌满水,背在身上。迈开步子,在大伯家的院子里“一,二,一…...”的来来回回走。
一日,大伯家来了客人,要杀鸡。大伯就对我说,“帮我把鸡逮住,水壶就归你。”费好大劲,我终于把鸡追累了。我拎着鸡的两膀站在大伯面前,“给,小鬼!”接过水壶,我两脚一并,朝大伯敬个军礼。“谢谢首长!”
哥按按架车的两轮,轮胎气足。他又走到前边,把挎肩绳紧到合适的程度。终于要出发了,“觉得累,就歇歇!”母亲再三叮嘱。“走了!”
随着老马叔的一声吆喝,老黑叔,哥和我出了小路巴向集上赶去。老黑叔走在前边,老马叔让我和哥走在中间,他走在后边。三辆架车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唤醒乡间的小路。微风轻拂,月亮疲倦地跟着。
当太阳走出地平线,我们已行程过半。太阳如同一位害羞的少女,涨红了脸,瞬间给乡村披上红装。周围光亮起来,一派生机。老马叔提议休息一会再走,我们把三辆架车停在路边。拧开水壶我喝了两口,转身递给哥。老马叔和老黑叔先后脱掉上衣,老黑叔上身黝黑发亮,老马叔的呈古铜色。稍过片刻,我们继续向北赶路。
大约早上七点半钟,我们连人带车走进了长官镇。那时的长官镇南北有两条长街,东西三道短街,比宋集大,也更热闹。街道上有三三两两的行人,事不宜迟,我们得抓紧时间找地方摆摊。老马叔和老黑叔已经来过几趟,他们让我和哥在东西街找摊位。在中间一道街东头的入口处,寻见一片空地,哥把西瓜车停好。
用事先准备好条帚简单清扫一下场地,铺上一块用尼龙袋拼接而成的单子,临时摊位就搞定了。把西瓜从架车上抱下来按大、中、小分三行摆好,将杆秤小心翼翼地放在人和西瓜之间。虽是逢集,菜市场上卖菜的并不多,因而前来买菜的人也不多。
哥在摊位前守着,我开始打量起街道的两边。对面有一家供销社,陆续有人进进出出。旁边是一家锅盔馍店,不时有炊烟袅袅升腾。不远处,沿街支一口大锅,旁边有两人,一人生火,一人忙着洗切东西。诸如动物的内脏置于案板,案板下是一张方桌,方桌上有少许调料品,碗筷之类的。
顺着西瓜摊这边看,身后是一家剪头铺子,颇为热闹!剪头师傅正在忙着,还有人排队等候。不远处有卖牛肉的,摊主头戴无沿的圆帽。听说长官有回民,此人大概就是吧。
“小伙子,西瓜多少钱一斤?”我回头一看,是一位中年男子。平头,圆脸,白色圆领衫,黑色短裤。“八分。叔叔!包熟,包甜。”我忙转过身来。“
给我挑两个。”“都一样好,刚摘的!你看,瓜把还湿着呢。”哥用秤开始称,“四十五斤!”哥喘了一口气。“
小朋友,算算多少钱?”中年男子望着我。“三块六!”中年男子话刚落音,我就报出了结果。“不对!你再算算。”
他故意逗我。“五八四十,进四,四八三十二。三十二加四,三十六。不会错的!”我大声说。又有人朝西瓜摊走来,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大妈。长脸,白净。一身碎花套装。
“阿姨,新鲜的西瓜,自家种的。”我用目光迎了上去。“挑个小的,家里人口少。”哥从后边称了一个,十八斤。“一块四毛四,阿姨!”
“西瓜看着不错,给我称四个!”声音真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帅哥,卷发,花褂,棕色皮凉鞋,小胡子,手指夹着烟,一条腿不停晃着。
哥选四个装袋去称,干提不动。“你去找个木棍来抬。”哥推了我一把。我看看四周,发现身后剪头铺子门前有把铁锨。“104斤!”“一百斤,八块。四斤,三毛二。八块三,二分算了。”卷发花褂付了瓜钱,一摆手,来了两人。他们一左一右把西瓜一抬,走了。我捏了一把冷汗,紧张的心慢慢平静下来。
太阳刚偏西,老马叔和老黑叔就拉着空架车远远走来。老黑叔脸黑得发亮,一层细密的汗珠挤在额头的皱纹里。老马叔边抺脸上的汗水,边朝我和哥挥手。我们的摊位上还剩三个西瓜。
街道除了守着的卖家,几乎不见人影。晃晃军式水壶,一点响动也没有。满满一壶开水,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被哥和我喝完了。老马叔说,先去填饱肚子,三个西瓜他自有办法。要去吃猪蹄了,我的肚子忍不住“咕噜咕噜”直叫。
“大叔,咱们去吃猪蹄吗?”我满心渴望,抬头看着老马叔。“吃猪蹄?你使劲想吧!”老黑叔伸出食指刮了一下我鼻梁。“走,大叔请你喝心肺汤,一毛钱一大碗!”
老马叔用手一指。不远处的那口大锅正冒着热气,我真担心太阳会掉进锅里。“老板,心肺汤四碗!”“哟,是你啊!又来卖瓜啦?”看来老马叔和他挺熟。“是啊,还有三个没卖。要不?便宜点给你。”“上次买你的,还有二个呢。”
卖心肺汤的摆了摆手。等哥买来锅盔馍,四碗心肺汤已经好了。锅盔馍两面焦黄,中间又白又软。吃一口锅盔馍,喝一口心肺汤,我早已把吃猪蹄的事忘到九霄云外。“老板,再来一碗!”老马叔能干也能吃。“待会咱到长官粮站门口转转,那里应该有排队交公粮的。”吃完第二碗,老马叔抺了一下嘴。
粮站门口果然有排队交公粮的。“俺侄,这回就看你的啦!”老黑叔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拉着三个西瓜走近交公粮的队伍。“青皮西瓜大又甜,解渴还能省饭钱!”喊罢,我回过头,老马叔朝我伸出大拇指。
“西瓜,便宜了,六分钱一斤。”我又喊了几声。卖完三个西瓜,太阳西沉,我们拉着空车向南往回赶。晚风一吹,临艾河的水哗哗直响。水中金色的光带在水波冲击下向周围散去,那闪闪发亮的碎光,像极了夜空中的星星。
那年,我九岁,哥十八岁。光阴如梭,日月似箭,三十八年过去了!古稀之年的老马叔腰弯了,渐浙认不得我!老黑叔也多年没见,不知可好!哥的头发全白了。年近半百的我每次路过西瓜摊,心底蓦然升腾起清凉的甘甜,久久挥之不去。路边的叫卖声依然那么熟悉,那么亲切!它来自久远,响在当下,必将不绝于未来!
李伟,艾亭中学教师,临泉作协理事,阜阳市作协会员。作品曾在《奔流》,《阜阳城市周报》,《颍州晚报》发表。偶有获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