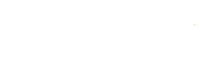文章来源:
公众号:有刺
公众号:重庆媒神
公众号:北京皇城相亲征婚
一秒四拍的迪斯科从大音响里震动而出,71岁的李明德最喜欢在这个时候,搂上一个女人,在北京菖蒲河公园的舞池里,与她身体紧贴,随鼓点震动。这能让他暂时忘记年龄,忘记对亡妻的愧疚,还有家中等他宰杀烹饪、独自享用的野鲫鱼。
北京天安门前的金水河向东流两百米后,改名菖蒲河,河道外围绿荫掩映,廊亭曲折,一二十年间,一些单身老人每周二、周六来此相亲。天气暖时,公园里几乎没有落脚的地方,几百个满面沧桑的男女在这里游荡、闲谈、打牌、跳舞,眼里却满是戒备和打量。
李明德60岁就开始在这里玩,前后交过五六十个女朋友。他一米六的个子,微胖,跳舞的时候,喜欢戴墨镜,鲜红的围巾在胸前飘,头上还歪着一顶船型军帽,正中镶一颗红星。
“我就是喜欢女人”,对此他毫不避讳,甚至有点张扬。他热情,每次都从家里用电动车驮着音响来义务播放音乐。
几百米外,天安门城楼画像上的主席还时常被这里的老人们提及。这些老人走过了特殊的人生道路,接受了“不完整的教育”,“耽误的社会生活”,并遭受了“经济转型的困窘”。
与大多青涩而糊涂的初婚不同,黄昏时分,他们走出曾经熟悉的集体和传统,来到公园里自由的相亲市场,寻求最后的伴侣。
不如跳舞
舞曲换成了情歌,李明德怀里换成一个四十几岁的女人,她身材还未走样,穿紧身的豹纹衣裤,同样戴一副墨镜,红唇,蓬松的卷发及肩。李明德右手搭在女人腰间,左手抓着女人的手,身体紧挨,舞步暧昧。几个拍子过去,女人在李明德的托扶下向后倒去,几乎要贴到地面,然后又猛地起身,摆头。
李明德喜欢跳舞,尤其到了夏天,女同志的衣服就一层纱,身体挨着,很容易产生感情。夏天他喜欢每天换一件花衬衫,这样离得再近也闻不到汗味,别人嘲弄地叫他“假华侨”,他不在乎,心里可美。
58岁的方菲菲住在菖蒲河附近,离异后单身多年。刚来公园相亲角时她可不好意思,远远站着,看见街坊马上掩面走开。现在,她对这里了若指掌,一般只在舞池外站站,察言观色。她说,到了这个年纪,大家都是老油条了,交友不是轻易的事情。大多数人都像她一样,怀抱希望,消磨时光。
这里的女人身上多少有一抹亮色——大红的帽子,玫红的围巾,明黄的羽绒衣,但最吸引男人的仍是年轻女人和新面孔。方菲菲笑说,“每次有新人来,人就都围过去了,真是跟苍蝇一样”。
65岁的王玉兰是个爽直的东北女人。每次来相亲,她都穿上价值上万的褐色貂皮长大衣,戴貂皮帽,画上黑色眼线和大红色口红。她和女儿一家四口住在一起,倒两趟公交车过来,每次都告诉闺女“去遛弯儿”。
她目标直接,“就三百万,房子也不要了,人就是你的了,伺候他,给他洗衣做饭,命都可以给他。”可追求她的男人,她都看不上,“好多人来跟我聊,也不撒泡尿照照,我理都不理他!”
重庆人孟文彬75岁,在这里算高龄。他对找老伴基本不抱希望,但求跳舞解闷。他腿脚不利索,步子碎,去邀请一位五十出头的女士跳舞,人家说“跳累了,歇会儿”,他笑笑走开了。“那就是拒绝你了”,孟文彬说,“‘歇会儿’就是委婉的说法,这是社交用语,一听就明白了”,谦和的笑意在他脸上的沟壑间回荡。
相亲角鱼龙混杂,但渐渐地李明德总结出来,来得最多的是北京男人和外地女人,这种组合的成功率也最高。据他所知,这些年在相亲角谈成结婚的大概有20多对——不少外地女人由此拿到了北京的户口,男人的房。“那么大年纪有什么爱呀”,他已见怪不怪。
孟文彬终于找到一个舞伴,对方是个五十多岁的北京女人,烫发,黄色马尾,戴个墨镜,脸上的皱纹还不多。但没跳几步女人就不乐意了——孟文彬步子慢,手举不高,转圈时老弄乱她的头发。他们换成了舒缓简单的舞步,顺势聊起来。
“你退休了?” “是。”
“退休金有多少?”孟文彬尴尬地笑笑,不回答。
“挺多的吧?” “不多。”
“不多是多少?”孟文彬只能笑着说,“五千多”,带着点歉意。在菖蒲河,最吃香的是八千以上的退休金,五千只能属于第二档。
一曲尚未终结,他们俩就分开了。
几百米外的中山公园,白发相亲角已为人熟知,老人如赶集般把孩子的资料打印在纸上,单身的年轻男女被“市场价值”排序,待价而沽。
在菖蒲河,也有属于老年人的“鄙视链”:北京>外地;无病>慢性病>动过大手术;自有住房>自有房与子女住>祖产>没有房;丧偶>离异>单身。
据2010年人口普查的抽样资料推算,中国60岁以上单身老人约有5200余万人,其中,丧偶独居者约600-800万人。研究显示,单身老人面临着比常人更高的健康风险,其中,丧失伴侣、独居者的境况更为严峻。
李明德找过政府办的婚介所,两回。但连着介绍的几个人,最后都以各种理由消失了。别人点醒他,婚介所介绍的都是托!他恍然大悟,“我一回忆,那女的表情就特虚”。
李明德的妻子是在21年前去世的。1996年8月,他与妻子结婚三十周年,两个女儿在东来顺为父母摆宴席。结果第三天中午,妻子突发脑出血昏迷,送到医院,夜里12点就走了。夫妻俩经历过抄家、下放,三十年没在孩子面前吵过架。最后的年月里,她跟着老李做买卖,医生说她死在了过度劳累。
那段时间,李明德老以为妻子没走,一进家门就喊她的名字,然后愣住了,房间里空无一人。他瘦了,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落,渐渐秃了顶。
妻子去世第三年,他去景山公园遛弯,一个女人鼓励他学跳舞。
这几年,他的头发才又长了点出来。
李明德的女伴大多和他相差二三十岁。他喜欢和年轻的女人跳舞,带出去体面。也是因为一次惊险的经历:2016年夏天,老李跟一个六十多岁的女人跳舞,一转身,女人没回来,摔倒了,胳膊抬不起来,120、110呼啸而至。老李赔了2000多医药费,从此再也不敢跟六十岁以上的女人跳了。
(菖蒲河公园相亲角的舞池,几对老人正随鼓动的节拍跳舞。)
交换法则
一月的一个周六,王玉兰穿着貂,在菖蒲河公园的墙边晒太阳。一个高大的北京男人过来搭讪。两人相识一年多,一见面,王玉兰就问他,“钱准备好了吗?”
男人笑了,“这样,一百万再加一豪华婚礼,怎么样?”
“不行,涨了,三百万!三百万拿来,我这人就给你了,你杀了都可以,卖窑子里也成。”王玉兰故作严肃,说完拍拍男人的手臂。她的考虑是,300万,其中一部分把女儿的房贷还清,剩下的她拿着,跟老头一起终老。
“你要不跟她谈谈,她年轻,五十多”,王玉兰指身边另一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
“我就相上你了。”男人眯着笑眼对边上的人说,“我就相上她那狂劲儿了”。
在菖蒲河十来年,李明德也一直充当红娘。最开始,他拿本子记下大家的要求。现在他只看一眼,就知道对方要找啥样的。他明显感到,2008年以前,女人的要求不高,都是真心找伴儿。后来,外地人打工的工资涨到两三千元,北京的房价蹭蹭地涨,人心也跟着膨胀——现在谈成的,男方退休工资普遍在五六千元,承诺给女人房子。
“有一女的,一上来就跟我说,我看这男的退休金有八千,我喜欢他,你给我介绍介绍。我说这男的有什么好,年纪大,长得不好看,打扮不利索,你不是喜欢他,是喜欢他的钱。”
李明德的房子是六年前买的,南二环内,现在值360万,当年的4倍多。但这没有让老李在公园里的身价倍增——相亲的条件也随着房价水涨船高了。在没有交付真心前,他往往对女人说,“我没有房”。他希望用自己的人格魅力打动对方。
一对佳侣的故事常被菖蒲河公园的人提及。老李自豪地说,这还是他介绍的:男的是处级干部,76岁,工资9000多,女的是东北人,小他22岁,特别漂亮。女的一开始不太乐意,嫌年纪差太大。后来我劝她,“这是个大干部,保证经济上能帮助你”。下礼拜,跳舞没见到他们俩,我心想,估计是成了。后来男的跟我说,“上礼拜那女的到我家一看,觉得可好了,直接就不走了”。过了一个月,他们就一起住了。婚后,他把三居室的房子房本名字改上她的。房子在天坛,二环,起码值七八百万。现在他们每到周末就去天坛跳舞。
老李总结,“房子很重要”。但也要分不同等级,祖产、子女名下还是廉租房,男人往往一开始不明说。为这种事,有几对结婚的最后都吹了。
在老李娶媳妇那会儿,阶级成分的好坏才是重要的择偶标准。菖蒲河的老人们好多都是在那样的环境中,经人介绍,或组织撮合,嫁娶成分良好的“进步青年”。
李明德的成分不好,家庭是资本家,文革期间被抄了家。幸而在抄家前一年,他借着优沃的家产和热心肠,打动了住在破庙的岳父一家。“她特别苗条,皮肤好,白”,老李回忆,当时工程师、医生都追她。他买了五六十元的礼上她家;他是工厂的小组长,平时发奖金,每月多给她20多元。
后来妻子跟女儿说,“你爸就是拿钱把我买来的。”
改革开放带来了个性的解放还有钞票,也带来阶层差异。用来交换爱情的筹码不再是政治成分,而是票子和房子。
老李现在依然乐于用物质打动女人,给喜欢的女人买羽绒衣,光电动车就送了两辆。他在交往3年的河北女人身上花费最多——3200块给她割双眼皮,3000块给她老家的房翻了屋顶,还投资让她和当地女人开门脸,卖黑茶叶。
手头大部分钱都给女人花了,但他觉得值,“让她觉得这是李哥给我买的一纪念品,让她想着我。”
连着几天,一对男女在菖蒲河公园的舞池里跳得扎眼。
两人都戴墨镜,女人一头波浪卷黑长发,马尾随着舞步在背后晃动,黑色毛衣裙包裹着凹凸有致的身体,一条枚红色围巾胸前飘荡,丰满的胸若隐若现;男人紫色衬衫,橙色皮带,金戒指、金项链、金手表明晃晃地扎眼。两人相差十岁,相识近一年,男人告诉老李,再过一个月他们要领证了。
音响的声音震得人心慌。两人舞步和谐,迈步,转圈,手向上扬。阳光下,两人的手碰到一起,粉红色的指甲油和金色的戒指折射出灿烂的亮光。
被忽视的欲望
“砰砰砰砰。”
舞池里,李明德带着喜欢的女人跳起轻快的舞步,心跳加速。时辰正好,他感到身体起了变化,悄悄拿女人的手碰了一下那儿。
每半个月,他都会有类似的渴求。“这是人性”,他语气坦然。
在他交过的几十个女朋友中,最令他难忘的,是6年前认识的一个退休医生,姓崔,五十岁。那是他第一次真正体会到性的美妙。
性学家潘绥铭在谈到老年性需求时说,根据调研数据,老年人跟自己年轻的时候比性生活数量下降了,但同样是老年人,跟十年前比,性生活数量上升了。他说,这是因为老年人的“性觉悟”提高了。
常年在菖蒲河遛弯的单身北京大爷王有光说,性欲象征着生命力,“看见裸女没反应,都嫌累了,就快死了”。
公园里跟李明德谈得来的,无论男女,都会聊这方面的话题,大家并不遮掩,“至少有七成人对这个有要求”。
尽管性不会成为明面上的择偶条件,但有人因此离婚。一个女人跟李明德吐露过心声。那是个57岁的外地女人,和64岁的北京男人结婚,几个月就闹离婚,“她最后跟我说了实话,开始还行,后来一点不行了”,她受不了,又不忍心找外遇,最后只能离婚,男人给了女人6万元分手费。
后来老李再在菖蒲河见到那个北京男人,发现他不爱打扮了,精神远不如以前。有女人当面拿他开心:“老二不行还找什么女人!”
“这比打他大嘴巴还难受,可怜啊!”老李感慨。
随着肌体的衰老,性能力不可避免地下降了。老李说,天坛公园有几个有能耐的人,能搞到日本进口药,一罐60元,20粒。“吃了药时间长,激情劲儿大,但事后就不行,第三天开始就没精神了。”
“砰砰砰砰”。
因为吃药,衰老的心脏不堪重负,有人最后死在女人的胸口。
菖蒲河公园曾经有一个活跃的老金,61岁,退休前是门头沟的火车司机。他身体好,模样英俊,梳着一根大辫子,情人无数。2015年8月,他在做爱时心脏骤停,死了。
“我知道两个死在这儿。魏老头,60多岁,一个不行,吃两个。吃两个心脏砰砰的受不了。”68岁的北京人韩阿姨说。闲谈时,她和旁人讲了个听说的事:一个七十多的男的,5套房,女方四十多,两个人领了证,男的吃药,估计是心脏受不了,一年不到就趴床上起不来了,女的也不照顾,就找个保姆看着他,房子都是她的了。
李明德以前也吃过药,“喜欢这女的,不可能不在乎这一点。尤其年轻的跟我们这个年纪的做爱,就是看得起你。”但自从大辫子老金的事在菖蒲河传开,大家害怕了,“现在尽量不吃药了,自然起”。
老年人的情欲往往得不到年轻人的理解。
但情欲总是短暂的。给李明德带来性启蒙的崔医生,最终还是离开了他。崔医生喜欢给老李念爱情诗。只有初中文化的老李听不懂,总问她,这句是什么意思,那句又在说什么。崔医生烦了。“最后因为这个没谈成,她54岁跟在天坛认识的一个老头结婚了。”
(NHK拍摄的纪录片《一起跳舞》,将近90岁的老安,每天一大早出门跳舞,舞伴小魏五十几岁,老安非常喜欢小魏,别人和小魏跳舞都不行,他把自己的退休金一半留给老伴,一半给小魏。)
爱情就是随时分开
菖蒲河公园的老人渴望欲望带来的心跳,但已不再相信怦然间的心动。
爱情就是随时分开,亲情是分开舍不得,离异十几年的北京人宋阿姨总结。到了这个年龄,两个人之间就是“一堵墙”,已经没有爱情可言,57岁的她更想找一个年龄相仿、不再分开的伴儿。
孟文彬则用一种绝望的理性说,75岁再往上,想找到爱情,几乎绝无可能。“每个人内心深处很多差异”。此外还有子女、家庭等现实问题。他不再渴望性,更羡慕小区里的一对老夫妻,八十多岁了,每天牵着手出去买菜。
李明德觉得爱情是一种很神秘的东西,“人世间两人好真是缘分”。他在菖蒲河遇到那个河北女人时,对方才三十多岁。他早上下午都骑车去接她,给她送饭。“她说,怎么报答你?我说,你爱我就行了。”女人是在前门的饭店做凉菜的,辫子本来耷拉着,和老李谈恋爱后,辫子也扎高了,变得更年轻了,但她就是不愿意结婚。
“她是爱,但是不想当老婆的爱。”2016年老李被车撞了,她照顾了一个月。
老李给她介绍过两个北京男的,最后也没成。“她说她离不开我,我说,傻丫头得成个家了。”后来河北女人回老家谋生,至今尚未结婚。他们偶尔还会在微信上说说话。
东北人李文妹在舞池里旁若无人地独自舞蹈,她爱笑,笑起来带一点羞涩。她在脸上扑了粉,眼窝深,显得五官立体,细长柳叶眉应和着深蓝色眼线,细薄的嘴唇上一抹玫红。
一辈子没谈过恋爱的她,57岁的时候在跳舞时遇到了真爱。
2016年5月1日,李文妹去天坛公园跳舞,有个人总看她,1米78的个头,气质像个老干部,衬衫西裤,身材挺拔。
和所有恋情开始的那样,俩人见过几次面,单独吃过饭,“我说话叨叨,他就一直听着,我爱说,他也爱听”。三个月后,她回东北老家办事,他买了好几样水果,糖和零食,到车站送她,非要送她上车。
她觉得他大概是真心的。
“他斯文,对人温和,是我喜欢的那种。”李文妹一提到他,就笑得像个小姑娘。早年下乡在农场,迫于对方成分好,她无奈嫁给了一个不喜欢的男人。“他又抽烟又喝酒,我可膈应他”。男人最后喝酒喝死了,死时才40多岁。
2016年冬天,他们想到了结婚。李文妹去河北陪男人给他的亡妻上坟。男人炒了好多菜,用小塑料盆盛着,骑着电动车带上山。在前妻的坟前,李文妹对着墓碑轻轻地说:“大姐,你们这一页就算翻过去了,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你为大我为小。”男人很感动,在坟前抱了她,晚上睡觉时,还给她盖被子,“掖了又掖”。那是她从未体验过的温情。
“我们是互补型的,互相欣赏,见面都很开心。”男人还为她戒了烟。
但从河北回来,男人说去跟女儿说一声,再回来就不说话了。他们没再见面。
去年夏天,他在电话里说,他得了轻微脑梗住院了,李文妹想去照顾,被他阻止。他们的沟通仅限微信。男人很少说话,李文妹怕他闷,在微信上开导他,逗他,喊他“夫君”。有时她也生气,“我们俩都付出了,为什么要放弃呢?你这样是伤我,像拿刀捅我。别再折磨我了!”
李文妹删了他的微信8次,但每次他都加了回来,“他心里还有我”,这句话她重复了几遍,眼里闪过了柔情。
几天前,李文妹收到一张他发来的照片,她戴着大红帽子,正在公园里跳舞旋转。“那时候我都快回去了,他在那儿也不告诉我。”这张照片给她带来希望。几天后,她坐公交车从通州去宋家庄找他。
他瘦了,袖口黑了,身上有了烟味,手指焦黄焦黄。李文妹看了心疼,觉得他不该这么糟蹋自己。而他则像初次带女孩回家似的,紧张得一个劲去厨房倒水。
那天,他抹了两三回泪,说不找伴儿了,帮女儿把孩子带大就搬去老年公寓。
“要不你也不找,咱们就当好朋友。”男人说。
李文妹拒绝了。这可能是此生唯一的一次恋爱了。她不想就这样放弃。
她的安眠药只剩下两片了。
(菖蒲河公园相亲角,一棵大树的根部,有人张贴了寻友启事。这在相亲角并不多见。)
坐着快艇去八宝山
李明德的家里被各种物件塞得满满当当,各个时期的柜子、纪念品,不再使用的电器,家里因拥挤显得热闹,但都落满了灰,透露出衰败的气象。他的卧室有个旧式橱柜,里面有三种对付失眠的药,还有11盒烟。
又快过年了,他并不期待。女儿们总是把吃的搁家里,就出去玩了。“我年年年三十跟她们说瞎话,说我在郑州玩呢,别来找我。其实我都在家,不出门,年三十、初一、初二我都不出门,看人家搂着亲热,难受!”
孤独感总在午夜降临。北京的杨大爷说,最孤独就是无助的时候——“晚上睡不着觉,想喝口水,又懒得起来”。
62岁的肖明全退休前是房管局的干部,房子和钱都不缺,也不缺女人。夜深人静翻来覆去的时候,孤单寂寞,他总想过世的母亲,“想想人生短暂啊”。
72岁的葛慧文,一个人住在通州一套150平米的大房子里,女儿在英国,一年回来一次,儿子在中关村,偶尔来看。三年前老伴去世,她害怕得整宿睡不着,总觉得空荡荡的房子里老有声响,只有把放佛经的收音机打开,让经文的诵唱填满屋子,她才能忘记老伴最后时刻在浴缸里的那些沉重的喘息。
一份对老年人孤独感的国际研究显示,可能不少于三分之一的老年人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孤独感。
老人相亲核心是解决养老的问题。养老有几种,家庭、养老院、朋友活动、婚姻。但前三种都解决不了根本的孤独。婚姻是最完美的,但实现起来最困难,成功率最低,特别是不被子女理解。
“他们这代人的子女多是独生,比较自私,觉得父母的都是自己的。”李明德的两个女儿倒是很支持父亲。“她们还撞上过,我和女的在床上,没穿衣服,盖着被单,她们有钥匙,就进来了,一进门就退出去,说‘哟,爸,我给你买的东西搁厨房了啊’,就走了。”
女儿有时也提醒他注意影响。之前李明德在家附近的公园跳舞,街坊跟女儿说,你爸净搂着年轻女的跳舞,她们不爱听,让父亲去别处玩,“女人直接带进家,别在外面”。
夕阳西下,老年就像流沙,被风吹散,丧失亲人,丧失健康,丧失价值感和人生的意义。
而性与爱情,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丧失。
菖蒲河公园附近,老人跳舞后常去麦当劳聚会,老冯正拿嘴给一个漂亮女人喂薯条。每喂一根都引得在场的人大呼小叫。老冯的朋友肖明全说,“我们活一天少一天,这么疯狂,就是为了调整心情。还有什么乐啊。八宝山越来越近,差别就是走着去,还是坐快艇去!”
但欢愉和疯狂的麻痹只能是暂时。
跟李明德交往过的女人最后都离开了他,总是过几个月就找借口不来了。每次分手,他都有一两个月缓不过来。几年前,他放弃了结婚的打算。
他深爱女儿,怕结婚了女儿不再来看他。
妻子去世后,李明德把做买卖赚的180万给两个女儿分了,给她们一人买了一套房,自己留了50万,为最后一程做准备。女儿承诺,会给他找一个最好的保姆,比妻子还好的保姆。
李明德是回民,他相信死后人就回到真主那里去。像是回到一个怀抱。这给了他安慰。
下午三点半,李明德收起音响,绑到电动车后座,一个人骑30分钟回家。没了音乐,舞池里的老人顿时显得有点茫然,不久都散了。
晚上,在价值360万的房子里,李明德打算煮一锅鱼汤,和着电视剧把它喝下。
(菖蒲河公园相亲角的长廊,打牌也是交友和消遣的一大方式。太阳西沉,牌友们将转战王府井麦当劳,占据二层的两三个圆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