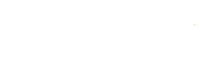徐冰 来源:中国青年报 ( 2022年01月25日 10 版)
---------------
1890年4月19日,契诃夫从莫斯科启程前往萨哈林岛。
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旅行。为给此行做准备,契诃夫阅读了大量有关萨哈林岛的书籍资料,据研究者统计有65种之多。这也是一场看上去有些神秘的旅行。在动身前一年的6月,契诃夫向曾去过萨哈林岛的女演员克·亚·卡拉狄根娜了解旅行路线及应注意事项,并要求她为之保密。
这还是一场引发众多不解的旅行。1890年1月,莫斯科的报纸发表了契诃夫将要开始萨哈林之行的消息,立刻引起众说纷纭。外人甚至契诃夫的家人都不理解,已经成名且事业正处于上升期的契诃夫,为何突然放下手头的创作,去进行一场对于他的身体来说堪称危险的旅行。也许是被问得有些无奈,在给友人的信中,契诃夫戏言,他“想要从生活中抹去一年或一年半”。
实际上,契诃夫为何要进行此次旅行,至今仍然没有完全破解。按照常规解读,契诃夫当时正处于精神危机之中。最了解他的哥哥的去世,给他造成严重的打击。他的创作似乎也遭遇了瓶颈。尤其是在1880年代,俄罗斯社会笼罩着万马齐喑的压抑。“怎么办”“往哪去”,成为很多人的迷茫与苦闷。契诃夫自然也处于这样的迷茫、苦闷之中,因此他的萨哈林岛之行,被认为是意在寻找“怎么办”。
坦率说,我不太认同上述解读。莫名感觉那样的说法总好似有那么一点没有捅破。的确,出于小说家的敏感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契诃夫的创作一直体现着“人民性”。就大的背景而言,他的萨哈林岛之行当然也是“到人民中去”。不过,假如以“代入感”的视角,我更愿意将契诃夫的这场旅行视为一场疗愈之旅。我更愿意相信,当时内心的苦闷,逼迫契诃夫必须走出去,正如同我们有时候也必须要出门几天一样。而契诃夫独特的个性,则使他选择了一条迥异常人的旅途。
这条旅途,很多人以为是熟悉的,因为不少作家已描写过它,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赫尔岑……但是,假如较真儿地再追问一句:真的熟悉吗?恐怕又很难说是。这一条旅途,就是那条通向西伯利亚的流放之路。
在当时的俄国,借助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作品的巨大影响,人们对流放制度背后所可能的生活已经有了概括性认识。但是这样的认识,粗浅甚至大多流于概念化。原因并不复杂,绝大多数人对于西伯利亚、对于流放生活,都没有切身体会。他们或从十二月党人的遭遇,尤其是那几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自愿追随丈夫走上流放之路,看到了某些坚贞与浪漫;或从“死屋”之中,看到了人性的堕落与残酷——这大约就是对于西伯利亚及流放的全部认识了。
但那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土地,几个概念岂能涵盖。这正是契诃夫让我敬佩之处:他从人们习以为常的自以为是之中看到了无知。他要亲身去体验,去看一看那片土地。而他选择的目的地更是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萨哈林岛在当时就有了流放地狱的恶名,可是在契诃夫之前,几乎没有什么人去探访过。
契诃夫在萨哈林岛上待了82天,据说填写了一万多张调查卡片,目前留下来的尚有7600多张。仅此就可体会到他每天的工作量是多么惊人。
因此这本《萨哈林旅行记》,在契诃夫全部创作中显得特别突兀。它与其说是文学作品,不如说更像社会学调查记录。套用现在相当时尚的一个词,这本书是契诃夫唯一的“非虚构”作品。书中充斥着大量的数据,有时不免让读者感到沉闷。但是作家的书写气质平衡了阅读的偶然不适,一旦进入描述,契诃夫独有的文学性立刻显现。这是伟大作家的个性力量,假如意识到契诃夫几乎以个人之力丰富、加深了人们对于流放的理解,就会更加感受到这位作家的伟大。
不过坦率地说,《萨哈林旅行记》正式出版后尽管也引发了不小争议,但相比于契诃夫整体创作历程,这部作品无论是在读者还是研究者中,都缺乏足够关注。人们知道有这部作品的存在,可除此之外也就没什么太多其他印象了。
我不知该如何理解这种现象。也许从文学的角度,不太好为《萨哈林旅行记》找到合适的位置。它更重要的价值,是在人们有意无意忽略的地方,发现生活的真实。而从时间性来说,我也愿意把这本书视为对抗遗忘之作。阅读《萨哈林旅行记》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萨哈林岛自己其实所知甚少。于是,新的阅读便由此开启,正如当时许多人因由契诃夫的这本书而开始了更深入的思索。
2022年01月25日 10 版
来源:中国青年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