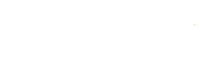9月的秦皇岛海边,秋日的凉意渐浓,海水也变成更为深邃的蓝。
贾樟柯的新片《一直游到海水变蓝》在初秋的海边举办了一场特别放映。
一早,阿那亚下起了雨。原本计划的海滩露天放映被迫转入了阿那亚蜂巢剧场内。
有迟到的观众在走廊席地而坐,也有前来度假的父母带着孩子一起观看。当电影中余华讲出“只要你给我发表,你要多光明我就可以多光明”的时候,我身边有一对头发花白的夫妇爆发出了畅快的笑。
这些跨越年龄和阶层的观众,就像他们正在观看的这部影片一样,呈现出某种神奇的镜像感。
影片中的一张张面孔与银幕前的一双双眼睛相撞,彼此凝视。这种凝视里带有中国人共通的记忆温度和乡土气息。
这是电影想要带我们进入的世界,一个不停流动的乡土中国。
在改名为《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之前,这部电影曾经用一个更为直白的片名《一个村庄的文学》揭示了它的关注核心——村庄、文学和文学性。
电影从贾樟柯家乡贾家庄养老院的一张张面孔上开始。
渐渐地,镜头从这些村民的面孔群像聚焦到四位从村庄走出的作家脸上。
山药蛋派代表人物山西作家马烽,生于50年代的陕西作家贾平凹,60后浙江作家余华,70后河南作家梁鸿。
四位作家,在时间上跨越几个时代,在地理空间上,更是贯通了东西和中原。贾樟柯有野心从村庄出发,以影像回望国人的来路,重新接续当代中国人与农村和土地的血脉联系。
影像与文学,在村庄上形成了交汇。
妙的是,关于农村与农民的乡土书写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发轫。
而这四位受访作家(已故作家马烽由其女儿代受访)中,梁鸿以《中国在梁庄》《出梁庄记》《梁庄十年》完成的调察式乡土书写,似乎从某种程度上与这部电影形成了一种更为紧密的互文。
从2010年第一本《中国在梁庄》到2021年关于梁庄的第三本著作《梁庄十年》,十年间,梁鸿用她的“梁庄三部曲”完成了一种带有人类学、社会学观察性质的非虚构乡土书写。
当我们望向梁庄,我们看到的,恰恰是贾樟柯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着力呈现的历史与村庄。
这一次,以《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为契机,我们与作家梁鸿聊了她的梁庄,以及她对影像形式乡村书写的感知。
梁庄
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的访谈中,马烽的女儿、贾平凹和梁鸿都提到过故土对创作的滋养。就像贾樟柯的诸多电影也都脱不开汾阳小城一样,故乡是电影和文学创作者永恒的母题。
梁鸿说,“童年和少年是每个人心中最永恒、最深刻的记忆。”
在踏上归乡火车的那一刻,梁鸿并不知道自己将会为梁庄写些什么,也完全没有预设过她的文字将从何处开始。“我只知道我要回家、要写一点东西,至于写什么、写成什么样,完全不知道。”
在北京开往邓州的火车上,十几个小时的摇晃之后,梁鸿抵达了家乡,迎接她的,是全家大大小小二十几张热切的面庞。
梁鸿非常久违地在梁庄住了整个暑假。“熟悉又陌生”,她这么形容自己重新回到梁庄生活的感受。梁庄变了,往昔记忆的房子、庭院全都改头换面,有的愈加豪华,有的极尽颓败。
梁鸿家的老宅,属于后者。
在梁庄,梁鸿父亲是最好的向导,借由他的指引,梁鸿一点点将记忆中的梁庄与眼前陌生的梁庄重叠起来。而那些被叠进时间褶皱里的故人和往事,也都在父亲的讲述中重新鲜活饱满。
“你原来听到的只是故事,当你看到这个人,听他讲自己的故事,看他的表情、看他生活的轨迹之后,你才知道,你原来离他很远。”当梁鸿回到家乡,见到那些乡土故事的主角,那些原本只从家人口中听来的人和事儿,才渐渐从远方的“故事”成为眼前的真实。
“人,真切地面对面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个时间的跨度之后就又不一样。”梁鸿说。
《中国在梁庄》里,父亲带着梁鸿在村子里转悠、回忆、不仅是重新认识村子里的老人,也是在重新辨认这个村庄从前的样貌。梁鸿用充满感性的笔触描写她眼中的村庄,也怅然地写“我记忆中的小河消失了”。
到了第二本《出梁庄记》,梁鸿的着眼点已经不再是“那条在村子变迁中消失的小河”,而是在轰隆的工业化进程中,从梁庄消失、外出的梁庄人。它少了感性的村庄抒怀,多了以人物为网的观察纪实,更像是纪实文学和非虚构人物访谈的杂糅。
就像是任何一部艺术作品都不可避免地要经历争议一样,关于“梁庄”的讨论也从未停止。其中最大的争论就在于书中“我”的在场感是否过于强烈,以至于削弱了非虚构写作的真实性?
这个问题,梁鸿曾经认真地思考过,“到底要不要我。是不是要纯客观的记录?”而思考的结果是,她坚持了“我”的在场。“因为梁庄就是我的故乡,这才是非虚构的真实。我不能假装他不是我的故乡,假装我不认识这个人,那反而是一种虚假。”
于是在书中,梁鸿毫不回避自己作为“出梁庄者”所经历的退缩、懦弱,甚至真实地袒露了自己不经意中流露出的高人一等的瞬间。
“那也是我真实生活的一部分,为什么不写?”
随着《出梁庄记》里的采访人物不断增多,梁鸿的感情也变得愈发复杂。“我们已经习惯了干净舒适的生活,看到那样破败的环境,会一下子特别不适应,会觉得很遥远、很异己,但这也就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这就是我们亲人的生活……”
就像是她书中写到的在西安蹬三轮车的梁庄二哥二嫂,他们生活的德仁寨,是一个房子密布、污水四散、不知何时就会被拆掉的城中村。“我”住在一个昏暗破败的小旅馆里,卫生间四处有着可疑的黄黑污垢,看似尚能支撑的热水器,稍稍一拉,店家自制的拉绳就断了,洗澡也成为奢侈。
两种环境的对照之下,“我”的不适透出难以掩饰的阶层差异。就像梁鸿自己说的那样,“我觉得我应该呈现出来。不管呈现出来的是勇敢也罢、复杂也罢,这些细微的情感非常重要,我觉得读者也都能感知到。尽管有些读者可能会骂我,但难道那不也是你自己吗?”
我是谁
在《出梁庄记》里,我常常能看到小武的影子,他在城市的边缘游荡着,试图寻找自己的出路,却又总是被困在原地、打回原形。
就像是书中二哥二嫂,从西安的一个城中村搬到另一个城中村,希望生活能稳定下来,却不得不接受必须要在各个城中村辗转的现实。他们心里清楚,城市永远对他们呈现出拒绝的神态,他们也从未想过要在城市安家。他们挣钱、回梁庄盖房,哪怕一年只能回去住上几天,似乎全年的辛劳也因此值得了。
那些出梁庄者,看似已经与梁庄的生活无关,却时时被梁庄牵绊,甚至,无论他们多么努力,赚到多少钱,也还是无法走出梁庄对他们的定义。
在梁鸿的书里,有一个不发一语却让人久久难忘的青年三轮车夫。在“我”拿着相机给西安蹬三轮的出梁庄者们拍照、聊天的时候,那个青年三轮车夫在远处冷冷地瞥了“我”一眼。那不仅是一个让读者难忘的眼神,更是一个属于梁鸿的震惊时刻。
“他一眼瞥过来,其实我自己特别不好意思。那一眼让我看到自己生活的差距,他自己生活的被定性,在我们的生活内部,他是被作为一个低层人来看待的,所以他才会有那种羞耻之感。而他看我那一眼,又让我意识到原来我高高在上,在俯视、定性别人的生活。
他让我意识到我的可悲、可鄙之处。我就是这样一个人,是代表那样一个阶层高高在上地俯视他们。我突然被阶层化了。”
那个眼神,梁鸿称之为,“那是整个生活赋予他的那一眼。”那一眼里,折射出的是整个梁庄系列中,一直伴随着“我”的身份困惑。
我问梁鸿,除了写作“梁庄”的过程,在当下的生活里她是否也会有自己的身份困惑时刻?
她的回答很微妙,她说自己只有在面对梁庄的时候这种身份困惑感才会特别强烈。“人的困惑感是多元的,在北京有了确定的生活、工作、家庭,这种困惑感可能反而没有那么鲜明。但是回到梁庄之后可能才会发现,啊,我原来不是那么确定!”
当面临梁庄,这位梁庄走出来的女儿也产生了她的疑惑,生活开始变得不唯一、身份也开始变得更多重,她也没有答案,但她相信“这种晃动、游移,恰恰是思考生活的一个开始、一个源头。”
这让人很自然地联想到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梁鸿的儿子坐在母亲故乡的小河边,对着镜头聊起他的成长和他记忆里的梁庄。这个14岁的少年,脸上稚气未脱却并不怯懦慌张,他聊起自己喜欢的学科,自己就读的学校和他希望成为物理学家的理想。梁鸿面对家乡时的那种身份困惑,在儿子身上,几乎难觅踪迹。
电影中,贾樟柯在画外音里让这位少年用河南话介绍一遍自己。男孩试了很久,似乎找不准那个音调。镜头静静地等待着这位苦思冥想乡音发声的少年。最终,梁鸿一字一句地用河南话带着儿子做完了他的自我介绍。
这是一个充满影像魅力的时刻。
梁鸿作为出梁庄者,她与梁庄的联系已经在稀释,依靠于父亲和兄弟姊妹来维系。在梁鸿的儿子身上,梁庄的印迹已经淡到几乎消失不见,甚至连属于梁庄的方言纽带,都几乎断裂。
或许面对梁庄,梁鸿仍然感到些许晃动和游移。但是显然,儿子已经很难有关于梁庄的身份困惑,那是母亲的故乡,而他是城市的孩子。作为出梁庄者的下一代,他生于城市长于城市,早已被城市所接纳。对出梁庄者来说,这或许是一种人生胜利,可是对梁庄而言,它正在被一个又一个梁庄新生命抛得越来越远。
他们的面孔
在梁鸿眼中,贾樟柯的电影充满文学特质,“具有提取深刻本质的能力”,梁鸿解释,“所谓的文学气质指的是某种深刻的可能性。它让你从一个普通的平淡无奇的故事、面孔里去提取某种本质性的东西。不是每个导演都具有这种能力。”
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里,当镜头中一张张平凡朴实的农村老人的面孔与我们相撞,梁鸿称之为“一个非常具有象征性的时刻”。
“那些面孔一张张过来,非常普通、转瞬即逝,街道上、小店里。它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那么普通的一张张面孔,突然具有了某种象征性。我们忽然意识到,原来那张面孔就隐藏在我们现实深处。原来他们就是历史的一部分。电影通过审美化的一个瞬间跟你的心灵发生碰撞。”
火花四溅的刹那,或许那张面孔没有足够的故事性,但却具有绝对的冲击力。“你可能会突然意识到‘原来他们是这样的’,‘原来这就是我的生活的一部分’。它可以被固定,被作为历史的一部分来思考、来呈现。”
电影中平凡普通的面孔与梁鸿书中的梁庄人一点点重叠,变成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人们,甚至,就是我们家乡的亲戚朋友。然后又在电影陌生化的魔法之下,给所有人一种突如其来的冲击。
“电影就是这样的一个震惊时刻。哪怕是一个最普通、最平凡无奇的面孔,也值得在大银幕上突然间与你相撞。会火花四溅的。”梁鸿说。
二十多年前,贾樟柯第一次将镜头对准了县城的小偷小武。那一刻,我们也似乎经历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震惊时刻。震惊于原来一个县城小偷也有他值得被书写的悲欢。
“《小武》像是一个文学作品。一个潦倒的、困顿的、负面的人物,怎么样去挣扎,怎么样去表达,他就是一个文学人物。”梁鸿这样定义了她心中的小武。
从小武开始,我们聊到了在作家眼中,电影与文学的关系。与电影理论界曾经叫嚷的“电影与文学分家”不同,也与诸多影迷以为的“电影对文学有强烈依赖”不同。梁鸿谈到,电影与文学之间,是在“相互汲取养分”,她着意强调了这个“相互性”。
“很多作家会看文艺片、老电影。比如我看日本导演黑泽明的《乱》、《影子武士》……也很喜欢小津安二郎的电影,会研究它怎么样呈现出这种形态。当然不一定去模仿,但是能够从中感受到某种文学气质和精神的滋养。”
对贾樟柯这部《一直游到海水变蓝》,梁鸿不吝溢美之词,称之为“具有史诗性的纪录电影”。她分析影片“恰恰把我们时代内部的那种破碎、疼痛给呈现出来了,它不是一个宏大的象征叙述,而是非常个人化、象征化的一种表达,它触及了我们生活内部更加细微,更有本质性的内核。”
我想,所谓的时代的破碎与疼痛,恰如《一直游到海水变蓝》中被时代逐渐边缘化的乡村,还有不断被都市文学边缘化的乡土书写。而究其根本,还是贾樟柯电影中和梁鸿书中共同描绘的那些“被时代撞到的人”。
那些被时代车轮撞倒的人,他们还没看清自己的位置,就已经被这个世界定位了。就像梁鸿在采访中对“梁庄者”历史位置的描述。
“也许对他们本人而言,他们就是自然的生活着,他们不知道自己处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状态。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写作者,还是会有一个总体的社会观察在里面。所以必然地,我们会看到,他们其实就是被时代撞到的人。
虽然他们有的人侥幸也挣到钱了,也可能生活的也不错,但是从他们整体的生活状态和一个社会结构中的位置而言,其实还是一个相对边缘的存在。
并且在社会的关注度和观念内部,还是没有真正地把他们作为一个中心,也没有把他们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的重要存在来关注。这还是我们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的目力所及之处,“就好像乡村已经不存在了一样,但乡村还是如此地广大,还有那么多农民在生活。它不是不存在,只不过是我们的观念、我们社会的关注点不在他们身上。”梁鸿对乡村的情感如此深沉,她的回答又是如此直白而恳切,像是为影片做出了一个清晰的注脚和响亮的旁白。
电影与文学无法扭转时代的车轮,但却可以引领我们奋力地游过确定的日常生活,抵达被日常琐碎所遮蔽的内心深处。就像是余华在影片访谈中说的那样,书上说大海是蓝色的,可为什么我看到的海却是黄色的?
我跳下去游泳,我要一直游,一直游到海水变蓝。
或许,这,才是电影和文学之于村庄的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