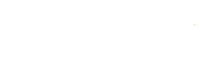来源:北京日报
1966年,红旗渠干渠建成通水。
红旗渠建设过程中的凌空除险作业。很多爆破工作需要在峭壁上打炮眼,工人们也是这个悬空的姿态。
排险队长任羊成在工地上的留影。他的门牙是被落石打掉的。
红旗渠工程中,干部始终冲锋在前。图为县委书记杨贵(前一)带领修渠大军上工。
林县人用钢钎铁锤挖开了太行山。
蜿蜒在太行山腰的红旗渠主干渠。
太行山,可能是中国最富神话色彩的山峦,盘古开天、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故事……在这里流传了几千年。
盘绕在巍巍太行半山腰上的红旗渠,也像神话一般传奇。站在渠埂上,抬头,是陡立千仞的悬崖;俯首,是深达百米的峡谷。渠水悬在半空,静静流淌,像一条天河。
流传了几千年的神话故事,出自古人天马行空的想象;流淌了半个世纪的红旗渠,出自劳动者坚韧不拔的实干。
上世纪70年代,周恩来总理曾经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新中国有两大奇迹,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一个是林县红旗渠。”不同的是,南京长江大桥的建设是举全国之力,而“红旗渠是英雄的林县人民用两只手修成的”。
放诸今日,在英雄常被庸俗解构、理想信念会被现实消解的时候,红旗渠就像一个英雄主义、理想主义的符号,高悬在太行山上,让人仰望,更带给人精神力量的震撼。
水之困
众所周知,红旗渠是为干旱缺水而修。带着这个印象去河南林州,不免会有一种预设:那里是一片干旱的土地,黄土、丘陵、荒山该是常见的景象吧?
出乎意料的是,坐在从安阳到林州的长途车上,沿途满眼都是绿色。路旁的绿化带草木葱茏,田里的玉米密不透风,一片墨绿。随风轻摇的玉米叶反射着阳光,田地仿佛一块巨大的翡翠,熠熠生辉。渐行渐近的山峦也被植被严密包裹着,生机盎然。
眼前的林州看不出一丝干渴、荒凉之象,绿化、植被不输于任何一座北方城镇。每个林州人都自豪地将这些绿色归功于红旗渠。
红旗渠风景区管委会副主任李蕾当过多年的讲解员,还曾在央视《百家讲坛》上讲述红旗渠。介绍当年林州的缺水之困时,她可以信手拈来大量的故事、事例。比如林州十年九旱,水贵如油,人们不得不翻山越岭去挑水吃。桑耳庄村桑林茂,大年除夕爬上离村七里远的黄崖泉担水,等了一天才担回一担水,新过门的儿媳妇摸黑到村边去接,不小心把一担水倾了个精光,儿媳妇羞愧地回屋悬梁自尽了……
只是,这些凄惨、悲凉的故事,早已成为历史,听上去距离眼前的林州实在遥远。红旗渠发挥作用已经半个世纪,绝大多数林州人早已习惯了它的惠泽。那个干旱缺水的林州,仿佛只存在于先辈们的讲述之中。
记者对红旗渠通水之前的林州更真切的认识,来自李蕾的一句问话:“从安阳过来的一路上,你看见水了吗?”
回想一下,几十公里的一路上,记者竟然没有看到一条河流、一片池塘。在千百年逐水而居形成的北方城市,这么长的距离见不到地表水,极不寻常。
但是,就此说林州没有河流并不确切。林州市境内有浊漳河、洹河、淅河、淇河4条河流,均属海河流域的卫河水系。只是这些河流都是季节性河流,一年中的绝大部分时间处于干涸状态。而且,这些河流的河道都在林州的边缘地带,即便是丰水期,林州也只有很少的区域能得到滋润。
也许是天意弄人,洹河出了林州不久就变得丰沛起来。距离林州最近的城市安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殷墟遗址就坐落在安阳的洹河之滨。
地表水匮乏,地下水更是难觅。地质资料表明,林州位于太行山地及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也是黄土高原的东沿。西部地壳以上升为主,而且侵蚀成密集的沟谷,太行山东侧断层较多,地壳十分破碎,像漏斗一样排泄着浅层基岩中的水分。
根据林州地下水勘探的资料,整个市域内,可方便开采浅层地下水的区域只有8平方公里左右。其余地区的地下水,多贮藏于山丘区及盆地的灰岩地层中,埋深多在200米以上,且地质结构复杂,开采难度大,代价高。直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这些地下水才少量得以开发利用。
在红旗渠通水之前,林州最仰赖的水源就是雨水。这里的年平均降水量672.1毫米,在北方地区并不算很低,但受制于特殊的地质构造,雨水降下来却留不住。“靠天吃饭”的林州,似乎很少得到上天的眷顾,雨降得多一些,便是顺着山势奔腾而下的洪涝灾害,正常年景之下,雨水会很快流走、渗漏殆尽。因而,干旱缺水就成了这里的“正常年景”,“十年九旱”成了最写实的描述。
干旱给林州祖辈留下了悲苦的历史。在以农业为主的年代,大旱绝收、小旱薄收,多数岁月里,林州人过着“糠菜半年粮”的日子。
据1995年版《红旗渠志》记载,在红旗渠修建之前,林县(1994年之后撤县设林州市)550个行政村中,有307个长年人畜饮水困难,有一百多个村要跑5公里以上取水吃。林县每年因取水误工达480万人,超过农业总投工的30%。也就是说,林县人每年要把将近4个月的时间,抛洒在那些漫长的取水山道上。
林州有一种独特的历史遗存,叫“荒年碑”,那是历代林州人对干旱的记录。合涧镇小寨村的“荒年碑”记述清光绪三年旱灾的悲惨情景:“……回忆凶年,不觉心惨,同受灾苦,山西河南,唯我林邑可怜……人口无食,十室之邑存二三……食人肉而疗饥,死道路而尸皆无肉,揭榆皮以充腹,入庄村而树尽无皮,由冬而春,由春而夏,人之死者大约十分有七矣……”
那些干旱困苦的日子,随着红旗渠的滚滚水流而一去不返。而提到这条彻底改变了林州命运的人工天河,林州人都会带着感念说起一个人,“没有他,就没有红旗渠!”
他就是当年的林县县委书记杨贵。
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1954年5月,杨贵被任命为中共林县县委第一书记。那时的杨贵年仅26岁,却是一个有着11年党龄的老党员。1943年时,15岁的杨贵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从事党的地方武装工作。
成为林县县委书记之前,杨贵是安阳地委办公室副主任。他对林县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干旱——此前半年,杨贵是安阳地委派到林县的抗旱保苗工作组组长。
而今的杨贵已是耄耋之年,虽满头银发,却身躯高大,精神矍铄,说起话来声音洪亮,中气十足,仍是一口浓重的河南口音。
初到林县的一个场景,杨贵曾讲述过无数次:他带着工作组到马家山下乡调研,一路风尘仆仆。到了农户家想洗把脸,主人端上来一个铁洗脸盆。杨贵瞅了一眼,脸盆只有烩面碗大小,水还是半盆。这倒不说,这边厢洗着脸,那边厢不停地“叮嘱”:“您洗完脸千万别把水泼了,俺还等着用洗脸水喂牲口哩!”
杨贵说,林县给他这个年轻的县委书记准备了三道“杀威棒”:林县旱,林县生活苦,林县“要命病”多。
“要命病”指的是当地多发的食管癌、皮肤病、甲状腺等疾病。追究病因,还是因为缺水,饮用水水质差。三道“杀威棒”的根源就是一个:缺水。
林县的症结清清楚楚地摆在眼前,解决的途径再明显不过——兴修水利。但是谁都清楚,这条路绝非坦途。林县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与干旱不断抗争的历史,千百年来未见实质改观,新一届的林县县委能有什么良策?
杨贵到林县主持召开的第一次县委扩大会议,中心议题是转变干部作风,发动各级党政干部去“摸大自然的脾气”。
所谓“摸大自然的脾气”,就是深入实地调查研究,寻找解决缺水问题的办法。
一场大兴水利的人民战争在林县风风火火展开了。世代饱受干旱之苦的林县人民热情高涨,林县水利工程成效显著。
《人民日报》以《社会主义的脚步声》为题发表长篇通讯,报道了林县两年水利建设取得的成就:“从大禹治水到1944年10月林县全境解放,三四千年时间,林县只有一万多亩水浇地……从1955年冬到1957年秋,两年时间,全县水浇地扩大了16万亩,全县可以利用水利设施灌溉的土地达到23.7万亩。”
现在的中原小城林州,名气几乎都来自红旗渠。而杨贵告诉记者,其实在红旗渠通水之前十年,林县就因为山区水利工程而闻名全国。1957年的全国山区工作会上,林县被树立为全国典型,杨贵登台介绍了经验,还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签发的国务院奖状。
当时主持这次会议的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表扬林县抓住了山区工作的主要矛盾,夸杨贵讲得生动,“有了水,闺女就往山上走,没有水,山上青年就找不到老婆。”
带着全国山区工作会上的荣誉和鼓舞,杨贵回到了林县。当年底,林县县委提出了比解决缺水问题更具气魄的目标:“重新安排林县河山”。
“人定胜天”,是那个时代的人们笃信的信条——放诸今日,这个观点也许值得商榷,但在当时,这却是中国人满怀激情建设新社会的豪迈宣言。
几年后,比林县更著名的全国典型大寨,也提出了同样的口号:“重新安排昔阳山河”。杨贵笑着回忆,这句话是陈永贵从林县学去的。
杨贵带着专程来学习的陈永贵参观工地。“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漆在峭壁之上,每个字都有数丈高。陈永贵一看就激动不已:“这个口号提得好,有气魄,鼓舞人。咱昔阳的山河也要重新安排。”
不过,在“重新安排林县河山”最初的计划之中,并没有红旗渠。杨贵回忆,那时候有很多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像“让太行山低头,让淇、淅、洹河听用”等等,但是眼睛都是盯在林县境内。林县挖了英雄渠、天桥断渠、淇河渠等几百公里长的引水渠,修建了要子街、弓上、南谷洞三座水库,水利工程的规模前所未有。
“护身符”
1958年11月1日,杨贵到新乡参加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晚饭后,他到驻地附近的一家浴池,准备痛痛快快地洗个澡。在水无比金贵的林县,洗澡都是一种奢侈。
刚把身子泡进澡堂子,雾气腾腾的浴室门口忽然有人高喊:“杨贵同志在里边吗?”来人是新乡地区公安处处长高雷,杨贵赶忙答应。
高雷紧接着喊:“快穿衣服,有急事!”
杨贵顾不上擦干身子,湿漉漉地套上衣服,就跟着高雷上了吉普车。这时,高雷才告诉他,毛主席的专列到了新乡火车站,毛主席要和地、县委的同志座谈。
回想起那次与毛泽东的谈话,杨贵至今仍难掩激动。他说,毛主席的话让他心里有了底,这才敢继续大干水利,不然也不会有红旗渠那么大胆的设想。
那时的林县和杨贵,已经由全国山区工作的先进典型,变成了“大跃进”的“后进分子”。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以大炼钢铁和“放卫星”为主要指标。林县偏偏这两项“核心工作”都没做好。
地委要求上报1958年的夏粮产量,杨贵最初如实报亩产114斤。领导不满意,几经引导,让他加上新麦水分,杨贵大着胆子加了一成,亩产增加到125斤半。而临近的市县却是亩产几百斤、上千斤地往高里上报。数字报得越高越“先进”。
林县山里有矿,山上有林,是新乡地区大炼钢铁的中心之一,可是一炉能用的钢也没炼出来。而杨贵焦虑的却是大炼钢铁抽走了几乎所有的精壮劳动力,水利建设无以为继。
见到毛泽东,杨贵直言不讳地“放了一炮”。
毛泽东知道这个小小的县委书记,一见面,就握着杨贵的手说:“林县杨贵,听说你治水很有一套。”
座谈开始后,毛泽东先向在座的河南省、市、县负责人问起了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的情况,杨贵据实回答。在浮夸风盛行、全国各行各业争相“放卫星”的形势下,杨贵的话让旁边的人捏了把汗。非但如此,杨贵还当面向毛泽东“抱怨”起来:“林县这几年兴修水利,今年大秋作物长得很好。可是精壮劳力都出来炼钢铁,庄稼顾不上收,棉花顾不上摘,丰产却没有丰收。”
出乎意料的是,毛泽东不以为忤:“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大办水利,办钢铁的劳力要撤下来。”说着,还伸出巴掌做了个“砍”的手势。
这之后,第一次郑州会议召开,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进行了一些纠正。不过,这次会议仍未摆脱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不切实际的估计,粮食、钢铁等产量的指标继续被提高。
但是在林县,因为有了杨贵在专列上与毛泽东的那次座谈,大办水利有了“护身符”。土法炼钢的小高炉只留下少数人维持,几万劳动力重新回到了水利建设工地。
到1959年,林县基本形成了南、北、中三个水利灌溉体系。那一年夏粮的大丰收,也印证了这些水利工程的效用。林县县委已经准备宣告,几千年的缺水问题被解决了。
但是丰收的喜悦还没有散去,一场大旱再次降临林县,已修的水利设施无水可引,无水可蓄,在最需要它们发挥作用的时候却成了摆设。林县人又开始了翻山越岭挑水吃的日子。
干旱带着几分嘲弄地告诉林县人,林县的山河远没有如他们所愿地被重新安排。
引漳入林
此前几年兴建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却没能使林县摆脱缺水的命运。这些是“无用功”吗?杨贵不这样认为:“倒应该感谢1959年那场干旱,它让县委从陶醉中清醒过来。我们对林县境内的降水、地表水、地下水进行了最大可能的利用,但水还是不够。这就证明只盯着林县,在家里打主意不行,逼着我们去县外找水。”
1959年6月,林县的旱情日益严重起来。杨贵和县长李贵、县委书记处书记李运宝带队出发,分别沿着浊漳河、淇河、淅河溯流而上,翻山越岭去上游寻找新水。
这样的组合让记者有些不解,找水这件事何需林县一二把手亲力亲为?杨贵说:“水在林县是天大的事。要想做事,领导干部就是要冲锋在前,这就是我们的工作方法和作风。没有这种做法,怎么带领群众往前奔?”
三个找水小组,一路步行,翻山越岭。很快,李贵小组和李运宝小组都失望而归,他们勘察了淇河和淅河沿线,水量皆不堪用。
沿着浊漳河一路攀山而上的杨贵,却有了喜出望外的发现。
起初,杨贵的脚下只有干涸的河道,怪石嶙峋。偶有潺潺细流,却远不足以为林县所用。直到进入山西平顺县石城公社,远远地就听见峡谷中的隆隆水声。
顺着陡峭的山崖攀援而上,杨贵等人终于见到了这条梦寐以求的浊漳河真容。峡谷足有百米深,河水在谷底翻滚着,波涛汹涌。大旱之下的浊漳河,竟然有这么丰沛的流量,杨贵又喜又气。喜的是这条河水量巨大,足以成为水源地;气的是上天何以如此不公,林县也有浊漳河,却只是条汛期才有水流的季节河。
浊漳河在林县附近的河道非常复杂,支流众多,水量不均。林县的浊漳河只是其支流之一,平顺县的浊漳河才真的是主河道。这条浊漳河常年流量为每秒30立方米,年径流量达到7.3亿立方米。
半个月后,杨贵带着足以改变林县命运的浊漳河资料回来了。到家的第一夜,杨贵兴奋得彻夜难眠,一遍遍地用红笔在地图上勾勒着引水线路。具体的引水点还有待详细勘测,浊漳河沿线标注的地名被杨贵圈了一个遍。这些红圈引出的红线,弯弯曲曲地汇集到了林县的一个点上——坟头岭。
每条线都穿越着巍巍太行的层峦,这意味着未来的引水渠要面对的层层阻隔,工程难度和工程量可想而知。
其实,林县浊漳河是一条现成的河道,从这里引水甚为方便,但杨贵却弃之不用。只有了解林县地貌,才能明白杨贵的苦衷。
林县的浊漳河从地势低洼的县域北侧流过,坟头岭是横在浊漳河西南侧的一道落差百米的高台。林县在1955年建设的天桥断渠,也是利用了浊漳河的水源,但灌溉面积只有三千余亩,就是因为水往低处流,不可能往上爬过坟头岭。
从平顺县引来的浊漳河水,只要到达海拔较高的坟头岭,就能让林县西部广袤的土地得到水源。随后进行的引水渠线路详勘表明,平顺县浊漳河河道比坟头岭的海拔高出将近9米。有了落差,水就能流到坟头岭。
但是有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悬而未决。林县设想的引水点,不但出了林县,还出了河南省,在山西省平顺县。除了浊漳河,那里的水资源也谈不上丰沛,能同意把水分给林县一份吗?
杨贵一方面给河南省委打报告,汇报从山西引水的设想,请省委协调支持,一方面运作起了林县在山西的“高层路线”。
林县是革命老区,战争年代的太行五地委驻地。时任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就曾在林县工作,深知林县缺水之苦。在他的大力支持下,林县从山西平顺引水的计划一路绿灯。
1959年10月10日,林县县委扩大会议确定兴建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后来的红旗渠。不过,林县县委的决定虽然得到了上级的批准,却也在得到批复的同时被明确告知:资金、粮食方面不可能给予支持。
1959年的那场干旱,实际上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开始。此前罔顾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的大跃进,再加上自然灾害,造成了严重的全国性粮食短缺和饥荒。河南是三年困难时期的重灾区,对引漳入林工程确实没有余力相助。甚至在新乡地委给林县的批复中,还含蓄地进行了劝阻:“林县可根据自己的财力、人力,考虑是否兴建这个工程。”
但林县人的性格却像太行山的石头一样倔强,认准的事情绝不回头。在愚公移山的故事发生的地方,林县人要把这个故事重新演绎一遍。
杨贵回忆,当时有领导私下里劝他,语气很不客气:“你林县有多大荷包,要包这么大的粽子?”杨贵答:“我们有55万人。”
不过,杨贵也承认,林县对引漳入林工程的谋划过程,确实太过乐观了。
1960年的春节,林县县委没有休息,一班人聚在一起做“算术题”。
出题的是杨贵:“引漳入林人工渠全长七万一千米,宽八米,高四米三,上七万一千人,每人承包一米,咱们多长时间能修成?”
县委组织部部长路加林先表态:“老百姓盖五间房,也不过个把月,一人挖一米,也就三四十个土方,两个月怎么也干完了。”
县长李贵比较“慎重”:“山上石头不好挖,算三天挖一方,大概一百天吧。”
共识很快形成:引漳入林工程2月开工,大干三个月,争取“五一”建成主干渠。
千军万马战太行
1960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引漳入林工程正式开工了。
近4万名林县修渠大军,扛着工具,挑着行李,推着小车,从十几个公社向着浊漳河汇集。
最后确定的引漳入林引水渠路线,渠首设在平顺县侯壁断,主干渠渠尾落在林县坟头岭,全长71公里。
侯壁断的海拔只比坟头岭高8.8米,这也就意味着,渠道每延伸8公里,垂直高度才能下降1米。而沿途经过的山体,都比这条渠的海拔高出许多。渠道只能像盘山公路一样,时而挂在半山腰上蜿蜒,时而洞穿山体,穿山而过。
山势陡峭得近乎垂直,实在摆不开每米一个人的挖渠队伍,林县县委只能把施工人数缩减了一半。4万人沿着勘测人员用白灰撒出的线路图,在太行山上摆出了一字长蛇阵。
4万人,聚在一起声势浩大,但面对巍巍太行山,人又是何其渺小。工程真的开始了,林县人才真正感觉到了艰难。
工程建设之初,林县没有任何外来支援。他们的家底真的能撑起这项工程吗?
杨贵说:“那时候林县的家底可是个大机密,只有我和几个县委领导知道,对上级都瞒着。”
这个“家底”中,最重要的是3000万斤储备粮,那是林县趁着前几年的丰收积攒下来的。全国各地都在放卫星时,林县没有放,这些粮食可是实打实地存在了库里。
另一项“家底”是挪用来的。大跃进运动中,国家下拨了资金,林县有300万元存在专项户头。这些钱被林县偷偷地用在了引漳入林工程。后来此事被发现,有人反映到主管财贸工作的副总理李先念那里。李先念哈哈一笑:“这不是什么大问题,不用想得那么严重。动这笔钱合情合理。”这才给杨贵解了围。
杨贵说:“那时候搞工程不像现在先要算投资。我们不算这个。我们投入的是人,算一算粮食够吃,钱够买炸药、工具,那就干!”
林县很穷,真要给引漳入林工程算出工程预算,恐怕没等开工就打退堂鼓了。林县人又很倔,像移山的愚公一样倔,他们最大的财富是自己的双手。
红旗渠真的是林县人用双手挖出来的。
陡峭的山体上,根本没有大型机械施展的空间——即便有,林县人也用不起。他们用的就是镐头和钢钎。
山体上全是坚硬的花岗岩。钢钎竖在上面,几铁锤砸下去,往往只留下几个白点。林县自己生产的钢钎钢质软,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老红军顾贵山去找部队的老首长求援,搞到了一批抗美援朝时挖掘坑道剩下的钢钎。这些高标号的钢钎让挖渠大军如获至宝。他们舍不得将其一次性使用,而是截成几段,焊在原来的钢钎头上,一支变成了几支。
炸药是工程最大的资金花费。即便动用了专款,很快也捉襟见肘。林县人又打起了国家下拨物资的主意。用于农业的硝酸铵化肥,成分和TNT炸药差不多,挖渠大军对其土法改造,自己生产了几百吨炸药。
待到红旗渠全部完工后,林县才对整个工程的投入进行了核算。十年间,总干渠、三条干渠及支渠配套工程共投工3740.17万个,投资6865.64万元,其中国家补助1025.98万元,占总投资的14.94%,自筹资金5839.66万元,占85.06%。而这些自筹资金中,还包括了对修渠大军的投工折款——一个工一元钱,总投工3740.17万个,折合3740.17万元。
引漳入林工程开工时,杨贵正在郑州开会。直到20多天后,杨贵才赶回了林县,马上急匆匆地直接奔了工地。从坟头岭到侯壁断的总干渠施工现场,杨贵走了三天,越走越是心焦。
4万人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战线拉得太长,分散了力量,工程进展非常缓慢。而此前,林县对工程的艰巨性估计严重不足,“五一”建成总干渠的目标本就不可能实现。
到了山西境内,不少当地住户听说林县县委书记来了,又追着杨贵告起了状。天天放炮,像地震一样,把牲口吓跑不说,还把房子也震裂了,这样下去还怎么过日子?原来,由于技术人员不够,民工又看不懂图纸,漫山打眼放炮,一崩一个山头,有的挖错了地方,有的炸坏了渠底。
从山西折返回来,杨贵马上在工程总指挥部召集了县委扩大会议。杨贵回忆说,这次会有两个作用,一是鼓劲,群众的热情和干劲已经调动起来,但是“五一”建成总干渠是不现实的,不能因此就泄气。第二是调整战略,集中力量突击山西境内的20公里渠道,修一段渠,通一段水,以通水促修渠,鼓舞群众。
事后证明,这次调整对修凿红旗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开工8个月后,引漳入林第一期工程,即山西段工程竣工通水。仅仅这一段,林县人就斩断了45座山崖,搬掉了13座山头,填平了85道山沟……
滚滚浊漳河水流到了林县边上,浪花拍打着林县的大门,极大地振奋着林县人继续修渠的热情。正是这种修一段、成一段的分段施工模式,才使得红旗渠的建设能前后坚持10年之久,并最终得以全线贯通。
也正是在那次林县县委扩大会议上,引漳入林工程被赋予了一个更催人奋进的名字——红旗渠。
为有牺牲多壮志
在红旗渠山西段的施工过程中,林县失去了一位重要的技术员——工程技术股副股长吴祖太。
在王家村隧道施工过程中,洞壁出现了裂缝。这条隧道的地下是砂石松散结构,为增加安全系数,负责施工设计的吴祖太已经将单孔隧道改为双孔,以减小跨度。但是3月28日收工时,工人们向吴祖太反映,洞壁上出现了裂缝。
吴祖太知道这是塌方的征兆,但仍然坚持进洞查看。塌方果然发生了,吴祖太再也没有走出来。
吴祖太当时还不到30岁,毕业于黄河水利专科学校,是林县少得可怜的科班出身的水利工程人员。红旗渠的勘测设计就是由他担纲。
杨贵回忆吴祖太:“林县的每一处水利工程,都有他留下的心血。他走得太早了,太可惜了。”
杨贵至今仍清楚地记着吴祖太那张年轻、腼腆的面庞。
红旗渠选址详勘的过程中,吴祖太每天都在山上奔忙。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第一年,干部口粮是每个月29斤,不足支撑每天繁重的野外勘测任务。一天,杨贵嘱咐食堂蒸了顿肉包子,慰劳大家。一群人吃得狼吞虎咽。杨贵问:“祖太,吃了几个?”吴祖太不好意思地搓着手:“七个,嘿嘿。”
修建红旗渠,林县人付出的不仅是汗水,还有鲜血和生命。十年建设过程中,共有81人牺牲在红旗渠工地上。
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张买江到工地时只有13岁。他的父母都是第一批建设者,父亲在红旗渠开工3个月后,被爆破的飞石击中头部。母亲赵翠英安葬了丈夫,又把儿子带到了工地。公社负责人不答应,赵翠英说:“红旗渠水流不过来,他爹合不上眼。让孩子接着干吧!”
张买江成了红旗渠工地上年龄最小的建设者。人小体弱,他帮着烧水送饭,身体渐渐长高,他学会了石匠、铁匠活儿,扛起了最繁重的劳动。后来张买江又学了爆破,最危险的活儿也冲在前面……红旗渠修了10年,张买江在工地干了9年,被叔叔伯伯们称为“小老虎”。
“排险队长任羊成,阎王殿里报了名。”说的是干活不要命的红旗渠建设特等劳模任羊成。
落石和塌方,是红旗渠工地上最大的危险。为排除这样的隐患,指挥部成立了排险队,身材瘦小的任羊成第一个报了名,被推荐为排险队长。
任羊成最常见的姿态,是用绳索捆住腰,从悬崖顶上垂下去。他手持长杆抓钩,身上背着铁锤、钢钎等工具,一直下到红旗渠工地的头顶上。那里,有被炸药炸酥了、震松了的石头,任羊成要把它们清除干净。这个工作和排雷一样,置身最危险的境地去清除危险。
“我‘死’过五回。”任羊成说,“阎王殿里报了名,可是阎王不收我。”
这份危险的工作让任羊成丢了四颗门牙。那是一次除险过程中,一块石头正砸在嘴上。一排门牙被砸倒了,压在舌头上。任羊成张不开嘴,舌头也动弹不得。他从腰间拔出钎子,插进嘴里,生生把牙别了起来。随后吐出一口血水,四颗门牙随着被吐了出去。
他曾从半空中掉下来过,没有摔死,可是掉进了圪针窝(当地对带刺灌木丛的称呼)。工友们从他身上挑出了一捧圪针尖。
他长时间腰拴大绳悬空,身上被绳子勒出一条条血痕。血肉模糊,粘住衣服,脱衣服时要扯下一片血痂。磨得时间久了,腰上竟然结了老茧。
任羊成腰间的老茧,曾让穆青为之落泪。
1966年,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穆青到河南采访,先在兰考写了焦裕禄,随后到林县准备写红旗渠。他结识了杨贵、任羊成。只是采访尚未完成,“文革”爆发,穆青被电话召回北京。没能写成红旗渠,成了穆青念念不忘的一件憾事。
直到1993年,穆青再次来到林县,又见到了任羊成。这一次,穆青写了反映任羊成事迹的长篇人物通讯《两张闪光的照片》。文中写到了第一次见到任羊成的情景:“我问他身上是否还有绳索勒的伤痕?他说,还有。他脱下上衣,果然露出了一圈厚厚的老茧,像一条赤褐色的带子缠在腰际。我用手轻轻抚摸着那条伤痕,实在抑制不住自己的情感,眼里早已充满了泪水……这就是红旗渠精神!这就是我们民族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红旗渠的红旗
1960年11月,红旗渠主干渠二期工程刚刚展开,中央发出通知,全国实行“百日休整”,红旗渠被要求停工。
大跃进、浮夸风的恶果继续蔓延着,持续的自然灾害雪上加霜,逼迫着全中国勒紧裤带,基本建设项目已经全线“下马”。
中央有令,林县不得不遵从,但并没有完全执行:绝大部分民工回生产队修整,留下300多名青壮劳力,组成青年突击队,继续开凿二期工程的咽喉——600多米长的隧洞——青年洞。
“中央要求休整,是因为当时粮食紧张,停止工程建设,全力保证老百姓的生命。但那时我们还有2000万斤储备粮,够吃两年的。中央指示要执行,工程也不能停。青年洞的作业面很小,上不了很多人,即使在正常年份,也要凿很长时间。留些人先啃下这块硬骨头,等形势好了,再大批上人修明渠。”杨贵说。
他告诉记者,在三年困难时期,红旗渠的建设没有中断一天,而且在1961年最困难的时候,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
开凿青年洞时,上级经常派人下来检查。施工青年们在路边安置了观察哨,一旦发现有小车经过,立刻挥动红旗,示意洞内的人停止施工。等车走远后,又继续干。
这样暗度陈仓的“小把戏”给林县惹了麻烦。
1961年7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谭震林在新乡纠正“大跃进”造成的“左”的偏差,一听林县还在大搞红旗渠建设,非常生气。林县组织部部长路加林正在新乡开会,不但不认错还直言谭震林偏听偏信。一怒之下,谭震林指示新乡地委撤了路加林的职,随后召杨贵到新乡开会,准备把林县树成反面典型。
到了会场,杨贵先接到了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的纸条:“争取早发言,深刻检查,争取主动。”
杨贵知道,这是史向生在保护自己。这位省委领导一直尽自己最大可能地支持着红旗渠建设。青年洞偷偷施工最困难的时候,史向生还曾登上悬崖绝壁上的施工现场,慰问青年突击队。
但是杨贵没有做检查,而是情绪激动地讲起了林县的干旱,讲起了55万林县人为修建红旗渠的拼搏……
谭震林没有表态,会后马上派出调查组到林县了解情况。这之后,谭震林成了红旗渠的支持者,路加林的职务得到恢复,红旗渠建设又得以大张旗鼓进行了。1963年,红旗渠还被纳入国家基本建设项目。全凭自力更生进行了4年的红旗渠建设,有了来自国家的支持。
多少年过去,杨贵对谭震林始终满怀敬意:“谭副总理了解了林县的真实情况后,对红旗渠建设一直关心支持。后来‘文革’中造反派揪斗我,谭副总理还竭力保护我。”
1964年12月1日,最艰险的71公里红旗渠总干渠全线竣工通水。水进了林县,马上显示出效益。这一年,林县粮食平均亩产达到423斤,成为河南省第一个亩产超过400斤的县。
红旗渠建设并没有就此结束。浊漳河的水到了坟头岭,林县又将其一分为三,修了三条干渠。坟头岭由此改称分水岭。
这之后,还有59条支渠,416条斗渠,林县人要在自己的家乡织一张水网,滋润每一个角落。
正当林县准备一鼓作气建设配套工程时,疾风骤雨的“文革”开始了。
“文革”中,一些造反派诬蔑红旗渠是“黑渠”、“死人渠”。杨贵也被打成“走资派”撤职罢官,长期遭受批斗。
但是跟着杨贵修成红旗渠的林县群众心里雪亮,他们给关押期间的杨贵兜里塞鸡蛋,往他怀里揣烙饼,最后干脆把他从关押地偷出来,送到山西,后又辗转送往北京。不久,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几位记者联名写信给周恩来反映杨贵的情况,周恩来保护了杨贵。
1967年,杨贵回到林县,任革委会主任。他没干别的,还是接着修渠。
1969年7月6日,历经10年,总长1500公里的红旗渠工程全面竣工通水。林县人用自己的双手,战天斗地,彻底改变了干旱缺水的命运。
修建人工渠,人们常用开挖土方数来说明工程量,但在红旗渠,描述工程量的是这样一组数字:削平山头1250个,钻隧洞211个,架设渡槽152座……
红旗渠完工后100天,杨贵调任洛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又开始组织黑材料,声称要砍掉红旗渠的红旗。周恩来得知这个情况后,措辞严厉地进行了批评,明确提出:“红旗渠的红旗不能砍。”
这面红旗是砍不掉的。红旗渠已经成了镌刻在太行山麓的一座丰碑,留下一种红旗渠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
修渠时,林县人靠着这股精神排除万难,一往无前;渠成后,红旗渠激励着中国人的精神,给人力量,催人奋进。
四十多年过去,红旗渠汩汩流淌,依旧是林县最主要的水源。在供水之外,红旗渠还是一种象征和标志。在这里,人们的日常所用,从小吃、酒水到住宅小区,处处可见红旗渠的品牌。
红旗渠修成之后,杨贵的命运在“文革”中风雨飘摇。在周恩来的保护下,杨贵被调到北京工作,曾在公安部、农业部任职,1995年离休。
离休后的杨贵居住在北京方庄,他在自家院子修了个全北京独一无二的个人“水窖”。
“天上的雨水掉下来,我就存起来,可以浇花。”杨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