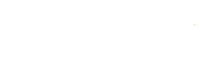医师们为了攻破新的疾病,为了揭开死亡的神秘幕布,逐渐涉足了被古人们所禁忌的“人体解剖学”,这些遗体标本虽口不能言,但却亲身讲述了曾经一例又一例致命的病毒、疾病。
人体标本制作师王耀,他的工作便是将自愿捐献遗体的人制作成人体标本,作为制作师,他究竟需要面对什么样的困境?这些自愿捐献的伟大灵魂,究竟于何处重新绽放?
他用一篇自述,为世界展现出多年从事这一行业为他带来的感受和经历。
鲜为人知的行业背后
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的嘉德堂,相比林立而起的众多教学楼显得冷清且阴森,略显古旧的瓦砾和残破的围墙把这里衬托得更加孤寂凄凉。
哪怕是学生们路经此处都会下意识地捂住口鼻,以免闻到福尔马林的味道。
很多医生都知道,福尔马林含有的37%~40%的甲醛,是一种有毒的物质,不慎吸入就有可能导致肺水肿,饮用过量甚至危及生命。
而在四川大学华西校区的嘉德堂,这种致命的溶液到处都是,这便是王耀的工作地点,一间狭小又空旷解剖室,生者与死者共同为医学奋斗的人体标本制作间。
王耀进入这一行完全是个巧合,在此之前,谈不上热爱,更谈不上了解。实际上,当年并没有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职业的体系标准,因此这个职位多数情况都是院系内部指派。
然而,没有多少人乐意整日面对尸体,不说尸体散发出的刺鼻气味,以及惨白而令人胆寒的面容,单是解剖、分割、拼接就不是一般人能接受得了的。
不过,待遇的优厚还是令王耀动心了,这对当年的他来说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
王耀在2008年接到了在解剖楼制作人体标本的工作邀请,在此之前,他一直只是一个华西医院血管科的楼层管理员,薪资并不高,生活很拮据。
但又苦于自身没有一技之长,正在窘迫之际,恰好这份制作人体标本的工作虚位以待。
王耀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想要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无可厚非,他想到了自己正在念书的儿子,又想了想早已年迈的母亲,还是决定尝试去掌握这么一门手艺。
王耀虽然不是医学生出身,但在华西呆了很久了,耳濡目染之下对人体血管构造和人体解剖结构早就有了一定的基础。
为了胜任这份工作,王耀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在教研室进行系统性的学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王耀认识了一些同行,也得到了不少旁人的帮助。
明白了这份职业并不像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容易,在逐渐深入的同时,王耀的性格也变得更加细心大胆了一些。
完成系统性学习之后,王耀又刻苦认真地研习了两个月,才终于拥有上岗资格,开始了自己的工作。
在王耀上岗后,尸体从接收、运送遗体到制作、保存标本到后期的保养和修复基本上都由他一人负责,偶尔会有解剖楼的老师会来这里顺手帮下忙。
但很多细节还是需要人体标本制作师本人去记忆,老师们也仅仅是帮着做些搬运和看管之类的小活儿。
如果旁人亲自下场解刨,反而可能令王耀的工作功亏一篑,帮忙的结果只能是帮倒忙,据自述显示,当年整个学校的医学系,无论是教学还是科研用的人体标本,基本都是出自王耀之手。
专业的挑战与心理的挣扎
人体标本制作师,听名字就不是一个简单的职业,王耀当然在选择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他从陌生到熟练并非一日之功。不过,在充分进入工作之后,还有更多挑战在等待他去克服。
王耀还依稀记得自己刚刚上岗不久时的经历,当时的他为了工作,不得不独自一人面对腐坏的遗体。
那天,不知是不是心理原因,王耀感到解剖室异常的安静,狭小的解剖室内只剩下钟表滴答声和自己慌乱的心跳。
作为一名经过专业训练的人体标本制作师,对职业的负责让他紧紧控制住自己的双手,令其不再颤栗,内心一边为死者祷告,一边安慰自己要相信科学。
王耀用特殊的刀具划开遗体的皮肤,然后一层一层地取出肌肉组织和结缔组织。可由于心理过于紧张,这个过程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意外。
他正在认真地处理尸体,突然感到有人拍打自己的后背,他很快意识到,这个狭小的解剖室里只有自己一人,本以为刚才是一种错觉。
没想到须臾间,冰冷的触感再次碰到了他的后背,他手中的工作顿时停了下来,冷汗刹那间涌上了自己的背脊。
望着逝者冰冷的面容,王耀再也忍受不住这份恐惧,尖叫着逃离了解剖室,解剖用的器具散落了一地。
他在解剖室外徘徊良久,迟迟不敢回去。但王耀又很快冷静下来,想了想,当时后背的触感十分冷硬,多半就是被仪器碰到了而已。
想通了这一点,王耀不由得松了口气,才察觉到自己有些大惊小怪了,这分明就是解剖室太狭窄的原因,往后这样的事恐怕免不了还会发生,怕成这样怎么工作?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鬼,胡思乱想只能是自己吓自己。
在脑中劝解完自己,王耀便抛开心中杂念,回到解剖室继续工作,而他的心理素质和专业技能也在日复一日的工作当中愈加精炼。
在身为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十二年里,王耀几乎时时刻刻都在处理工作相关事宜,这份工作本质上是没有固定的休息时间的。
因为制作标本所使用的每一具遗体都是由逝者捐赠,因此只要一出现遗体捐赠的电话打来,他就要跟着相关人员去搬运、处理遗体。
因职业需要,像深夜要求处理遗体一类的事件,王耀早已经见怪不怪了,但仍有一件事令之记忆犹新:
那天夜晚,一位老人刚刚离世,根据老人生前的遗愿,他的遗体将被捐赠出来用于研究,而王耀正是处理这位老人遗体的制作师。
老人的遗体是从医院运送过来的,遗体被一个裹尸袋封住,就在王耀和一名助手正准备将老人的遗体抬上冷冻柜时,意外发生了。
刚刚触碰到裹尸袋的时候,老人的遗体忽然发出了一阵阵声响,低沉的声音仿佛在念颂什么。
年轻的助手早就被吓得逃开了老远,紧紧地盯着裹尸袋,他的紧张也影响到了王耀,令王耀浑身发凉。
紧张错愕之际,王耀又想起之前在解剖室的经历,世上本就没有鬼神,何必自己吓自己?
于是,王耀本着问心无愧的心态,鼓足了勇气上前拉开了裹尸袋,这才看清楚,原来是裹尸袋中有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里面正播放着佛教超度灵魂的颂词。
王耀再次松了口气,冷静了下来,连忙招呼助手,给他解释了一番,这才将老人的遗体搬上冷冻柜。
但实际上,伴随遗体的工作往往都是如此,一些细小的异动都会无限提高人们内心的恐惧,这份恐惧也跟随王耀度过了相当一段时间,但身正不怕影子斜。
王耀始终对遗体怀有一颗敬畏之心,他坚信,世上没有什么是不能克服的,恐惧也是如此。
十二年坚守,生命之重
自从王耀发表这篇自述为止,他已经在人体标本制作师这个岗位上工作了十二年的时间,在这十二年中,这些偶尔被吓一跳的意外事件比比皆是。
但他从不逃避,而是时刻保持冷静,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
每当接到医院或红十字的遗体处理电话,都需要他尽快到场,他也愈发熟练地解剖着每一具尸体,平均每年能够处理的尸体高达50具。
据王耀本人所透露,即使工作已经非常熟练,他仍然不可避免地会对这些尸体感到害怕。
但这并不代表他的工作热情有所减退,这份职业虽然又苦又累,但其带来的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王耀经手的尸体形态各式各样,有的尸体大幅度烧伤,面容惨不忍睹,有些则是浑身僵直,面容发青,甚至有的身体组织已经发生腐坏,散发着重重恶臭……
这些无一不是对人体标本制作师的考验。
他们必须摒除一切芥蒂,怀抱着对大体老师的敬意,强忍住这些外部因素为自己带来的不适感,认真地做好每一个细节,清洗、分割、剔骨、拼接。
一遍又一遍,直到让这些令人尊敬的大体老师’重新燃起智慧与科学的灯火。
长久以来,许多人对接触尸体的行业感到晦气,若非不得已,往往不愿意入行,就连该行业中的老手王耀一开始也是因生活所迫才选择入行。
但难能可贵的是,王耀在选择这一行业之后,便拿出了十二分的努力,因为他明白,手中所持的手术刀将为这名志愿者雕刻出生命最后的夺目流光。
人体标本的未来——“活着”的尸体
在生物塑化技术到来之前,我国一直都在用福尔马林固定的人体标本在为学生们教学,但是由于福尔马林的高刺激性和毒性,很多医学院的教学环境都非常差劲。
中国解剖学会副理事长、大连医科大学解剖教研室主任隋鸿锦曾用一句话形容解剖学的课堂:“老师流着泪讲,学生流着泪听。”
正是由于这种教学环境,导致很多优秀的学生放弃了解剖学,甚至放弃医学,这让隋鸿锦心中非常无奈。
1992年,当隋鸿锦第一次接触到生物塑化技术时,他就意识到,这将极大地改善解剖学的教学和工作环境。
这种生物塑化就是指,先将人体浸泡在福尔马林数月用于杀菌固定,然后将人体解剖,剔除下容易腐烂的脂肪物等,这一过程长达两千小时左右。
接着使用丙酮脱水排除福尔马林,然后在真空中用硅橡胶或树脂熏蒸数月,当整个标本的组织液完全被置换出来,这具人体塑化标本便完成了。
这样的人体标本无毒无异味,只要保养得当甚至能够保持上千年之久。
1994年,隋鸿锦专程到德国学习了这项技术,并将其带回到国内,在隋鸿锦与一众人体标本制作师的共同努力下,越来越多的人体塑化标本被采用。
这让他意识到,也许这些人体标本不仅仅能造福医学生,甚至有可能进入公众的视野,为更多人科普医学上的知识。
从此,人体标本不再仅仅是医、学院的专属,他们走入了公众视野,为更多人讲解着人体的奥秘。
一位长期抽烟的中年男人曾走入展览馆,当他亲眼看着抽烟导致的癌细胞是如何一步一步腐蚀着标本时,他惊恐万分,并认真表示自己一定会尽量戒烟或少吸烟。
人体标本成为了一位言传身教的老师,这比任何教科书上的论文资料都要令人印象深刻,这些标本最真实,最深刻的案例将知识传授给人们。
以改善人们的饮食、作息健康,将更多的健康隐患扼杀在摇篮中。
以往人们总是讲究“入土为安”,对于死亡则闭口不谈,认为这是一种晦气,而在人体标本制作师的手中,许多人看到了生命不为人知的另一面。
原来人体在死亡之后,还能以这样的方式持续绽放。这意味着人们开始思考死亡之后的遗体价值最大化。
博物馆内,无数栩栩如生的标本向人们展示着生命的意义,对于遗体的捐献者而言,死亡不再是消极的、令人恐惧的,而是一个非常正常的、自然而然的过程,正如四季变化一样。
王耀就经常与遗体捐献者讨论有关遗体标本制作的有关事项,并且详细告诉捐献者们,在他们死后,制作师将会如何安置他们的遗体。
在交谈的过程中,他们对于“死亡”这个话题丝毫不避讳,捐献者们也很有兴趣听到那些事无巨细的安排。
王耀曾经接待过这样一位老人,他在得知死后的遗体还可以为国家做贡献的时候,竟然千里迢迢跑过来签署这份遗体捐献协议。
老人直言,死后若还能有人在遗体面前向自己鞠躬致谢,那就是自己最欣慰的事情。
迄今为止,中国人体器官志愿捐献数已经高达四百四十余万,他们怀抱着对美好的向往,将生命延续给一位又一位陌生的患者,将遗体奉献给医学事业的未来。
他们重新定义了“死亡”,并以实际行动告诉人们,“死亡”也一样拥有价值,且能够造福人类。他们在升华死亡意义的同时,也引领着无数生者对生命意义的思考。
无论是医生、人体标本制作师还是无私的捐献者,他们都在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方面面在为医学而奋斗。
他们奉献了自己的青春,奉献了自己的未来,甚至于奉献了自己的身体及一切,每一位愿为医学而献身的人们都是伟大的,这份伟大,值得敬佩。
参考资料
[1]《医学与哲学》2011年1月8日,《关于人体标本概念与伦理的思考》
[2]《文明》,2011年第11期,《“死亡博士”的人体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