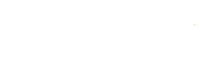明初洪武年间,江南曾有相当一批人徙入苏北。然而,对于这场移民的文字记载不仅少得可怜,而且十分零散,只是在民间广为流传。于是,有人怀疑这场移民事实的存在,或有人把传说内容当成完全的事实。本文试图把零散的文字资料和广为流传的口碑资料结合起来,加上可供佐证的其他相关档案资料来讨论这场移民的有关问题。民间把这场移民称为“洪武赶散”,我们则称之为“洪武移民”。
一、“洪武移民”的事实是否存在
家谱、族谱是反映一个家庭的家庭文献,自然是我们研究人口源流的最有价值的资料之一。从能见到的家谱、族谱中,我们找到了有关这场移民的资料。现藏于兴化施耐庵文物史料陈列室的《(咸丰)施氏族谱?卷首?序》中说:“吾兴氏族,苏迁为多,白驹场施氏耐庵先生于洪武初由苏迁兴化,复由兴化徙居白驹场。”“扬州八怪”之一郑板桥家族的《书带草堂昭阳郑氏家谱》记载,始祖重一,明洪武年间自苏州迁兴化。任大椿家族的《经训堂任氏族谱》记载,任氏原居苏州,元末迁兴,另有一支迁东台、一支迁宝应。邗江头桥《黄氏宗谱》记载,黄氏祖居姑苏崇明,明洪武年间兵燹,一支迁维扬安阜洲。高邮菱塘回族乡杨得良家谱记载:“始祖修生乃姑苏吴门人氏,当时太祖始起义兵伐苏??修生携眷北迁,道经维扬之北菱塘回回湾之地,爱其风俗,乃居之??。” 江都邵伯《王氏家谱》说:“本太原人氏??迁苏州,洪武初迁甘棠。”宝应《朱氏家乘》记载,朱氏原居苏州,洪武初由苏州迁宝应。《乔氏家谱》记载,乔氏始祖由山西襄陵迁苏州阊门外,明初自苏州迁宝应柘沟,后迁入宝应城。此外,邗江的《孟氏家谱》,兴化的《韩氏族谱》、《庆云堂徐氏族谱》、《风雏堂陆氏族谱》、《大禄阁刘氏族谱》都明确记载了他们的家族明初由苏州迁来。
咸丰以后的家谱、族谱常有攀附,因而可信度大打折扣,但上述所列家谱、族谱者是咸丰以前的。地方志书中对这场移民也有记载。民国《泰县志(稿)?卷二十二?氏族》记载了泰县一些家族的情况:“王氏原籍山西太原……自宋南渡始徙新安,后因兵乱复徙姑苏。明太祖统一海内,其先世伯寿思归土仍徙江北泰州之安丰场,此王氏迁泰之鼻祖也。”“吴兴沈氏”条下注“沈氏先世系出吴兴,明初沈有成由姑苏迁泰。”“湖州费氏原为浙江湖州籍,明初有名陶然者始迁于泰。”“苏州徐氏”条下注“徐氏系出颛顼??子孙散处四分,而苏州尤盛。明洪武初,张士诚据姑苏,有徐大岗者迁避于泰之北关外东坝坊。”民国《阜宁新志?卷十五》载“境内氏族土著而外,迁自姑苏者多。”民国《泗阳县志?卷二十一》载,席氏、唐氏、吴氏、朱氏于明初分别由苏州的东洞庭山、昆山、句容、吴县枫桥迁入。
语言是记录社会变迁的特殊档案,某种方言的形成与移民的影响有着极大的关系,移民史可以用来解释方言的部分成因;反过来,方言现象也可以为移民史提供佐证。苏北大部分地区的方言属北方官话中的江淮官话(包括洪巢片和泰如片),江淮话和北方话(狭义的)分界线是以有无入声为主要划分标准,江淮话保留古入声调类,以喉塞收尾,北方话入声消失。江淮话的北沿地带自东南向西为灌云北部、新浦、东海南部、新沂、宿迁东界里侧一个狭长条、沭阳大部、泗阳西部、泗洪大部,这和我们调查中听到自称来自苏州阊门的移民到达的苏北地区的北沿界线是基本一致的(我们在宿迁调查时,自称来自苏州阊门的就少得多,到邳县就基本上听不到了)。有资料证明,今江淮地区当时的方言和今山东、河南地区当时的方言是基本一致的。从《韵学集成》、《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国经》等历史语言档案资料来看,北方语的入声消失是在15世纪至17世纪初。明初,北方话中虽然还有入声,但已显出明显的消失的趋势。扬州、淮安等地,地处大运河畔,当交通冲要,南京又是明王室的政治中心,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江淮地区的方言也应当和北方话一样,入声逐渐消失。然而现在的事实是江淮地区的方言中入声得以保留,以苏州话为代表的吴语也有入声,而“苏州”移民在苏北地区的北部边界和江淮方言的北部边界基本一致,这就绝非偶然。民国《泰县志(稿)?卷二十五?社会四》中记载了一条泰县谣谚;“革丁革丁梆梆,革到杨家庄上,杨家庄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在这谣谚的注中说,“泰县方言 ‘我’字读成鼻音,若‘引’,则明洪武迁苏民于泰以后转变而成之音也,此‘我’字独作官音,与火叶,则此谣谚之起必在明前。”这里所说的泰县的地域范围相当于今泰州市海陵区、姜堰市的辖地,今这块地域的方言读此谚并不押韵,若按官话读则押韵,这就说明在明以前,这块地域的方言已接近官话,洪武年间的大移民使这块地域的方言发生了变化。直接的语言佐证材料,我们还可以举出若干,如古咸山两摄的今分类,北方话(狭义的)为一类,江淮话普通分为三类(南京方言两类),和吴语相同;韵母的高元音化、单元音化、鼻化也和吴语相同,这里我们不一一详细列举了。我们在苏北平原进行调查时,还听到一些关于这次移民的故事和传说。有关于这次移民的背景的,如说江南有一种大麻蜂(影射朱元璋,传说中他是麻子)螯人,人被螯即死,只有逃到江北才能避灾;有描述移民行进途中情景的,如说船行至江中,有江猪(谐“朱”)要吃人,常常将船掀翻,多亏船神保佑才能到达长江北岸,但江猪不死心,就在北岸掘岸,以至长江北岸时时坍江;还有移民与土著在体质上存在差异的,如说移民后裔的两脚小趾甲中有破痕或是灰趾甲等。这些故事或传说,孤立起来看近乎荒诞,但如果把它和这场移民的其他佐证和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它实际上反映移民们对这场人口大迁徙的态度,也间接地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关于这场移民存在的口碑档案。
二、“洪武移民”的历史背景
在元朝末年的反元大起义中,苏北地区是反元义军之一的张士诚部崛起之地,也是后来各路割据势力相互兼并的主要战场。在苏北,争城夺地的殊死之战时有发生,加上连年灾荒,苏北平原人口流失、户口凋零、田地荒芜,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明初,昔日繁华的扬州为朱元璋所得时,“城中仅余十八家”(《洪武实录》),这十八家也是“兵火之余也”(《嘉靖惟扬志》),“淮安仅存槐树李、梅花刘、麦盒王、节孝徐等七家”(民国《盐城县志》),这些说法虽说可能有些夸张,但当时苏北平原“地旷衍,湖荡多而村落少,巨室小,民无盖藏”(《嘉靖惟扬志))则是事实。明王朝要巩固政权,首先就得繁衍人口,恢复生产。明王朝为发展经济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其中之一便是有组织地进行人口迁徙。移民的原则是“狭乡之民听迁之宽乡,欲地无遗利,人无失业也。”规定对移民“给牛种车粮,三年不征其税;新垦田地,不论多寡俱不起科”。(《明史?卷七十七》)并鼓励种植经济作物。额外“益种棉花,率蠲其税。”(《洪武实录)》江南苏州、松江、湖州、嘉兴、杭州五府,由于占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经济较发达,人口也较稠密。这样,明王朝自然要把这里的居民迁往邻近居民稀少的江淮地区。明王朝的移民还有抑制豪强,打击、分散反明政治势力的目的。《明史》中所载的由苏松等五府迁入凤阳的移民,其中不少就是地主富豪,让这些富豪离开故土,也就使他们失去了原有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和政治实力。从扬州地区发现的家谱、族谱来看,徙往苏北地区的移民中也不乏富户。张士诚在苏北起兵后,苏北地区的人民曾不同程度地支持过这支义军,乃至直接参加起义部队,此后又随军渡江南下。张士诚待人又有“深仁厚德”(明?陆容《寂园杂记》),朱元璋攻打苏州时,苏州一带屡遭兵燹,因而居住在苏州的人都竭力帮助张士诚,“全城归附,苏人不受兵戈之苦”(明?陆容《寂园杂记》),以致张士诚能守城十月,使“明主百计不能下”(民国《盐城县志》)。思乡恋土是人之常情。中国又是个传统的农业国,要农民离开自己耕种的土地,自然有各种怨恨,一般百姓对这场移民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不能理解,把这场移民看成是纯粹报复的行为,认为朱元璋对张士诚的部队和苏州居民恨之入骨,以至“士诚兵败身虏,明主积怒,遂逐苏民实淮扬两郡”(民国《盐城县志)))。
三、苏州阊门与移民的关系
移民们大多数说自己的祖籍是苏州,并且确指为苏州阊门,有些咸丰后的家谱、族谱也直接言明他们这一家(或这一族)迁自苏州阊门。不过从移民在苏北的分布和数量来看,移民们都是阊门人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苏州阊门和移民究竟是什么关系呢?阊门是苏州八门之一,在苏州城的西北。出阊门西行可达枫桥和寒山寺,京杭大运河从枫桥和寒山寺旁穿过,是水路经苏州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京杭大运河是近代交通发展以前沟通南北的唯一水道,所以出阊门、入大运河。是苏州向北去水路的最佳路线。由于移民们要过江,所以必须走水路。我们在苏北平原调查时,移民的后裔也多说他们的祖先当年从水路来,有的地方至今还留有正月初二祭船神的习俗(上文的传说也提到,他们过江时由于船神保佑才能平安过江)。明代对户口、田赋的控制是较为严格的,明太祖于洪武三年创行了里甲制度,明政府又编造《黄册》(即户口总册),登记各户的籍贯、丁口、田宅、资产等。十年一更造,逐级上报,层层造册,直至户部,按朱元璋“凡赋役必验民之丁粮多寡,产业厚薄”之令,作为派征徙役的依据(《洪武实录》)。因此,这样由官方组织、发放凭照川资、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组织者自然要先集中被迁之民,登记造册,编排队伍。由于阊门所处的交通地理位置。官方也就很自然地在阊门附近的驿站设局驻员。办理有关移民的一切公务。旧时寺庙往往又是“慈善机构”,阊门外除寒山寺外还有几座大寺院,也就有条件和可能接待和临时安置来自苏、松等五府众多的被迁之民。阊门一带也就很自然地成为迁民的集中之地。成了他们惜别家乡的标志。从苏南迁往苏北的人们,寄居他乡,不少人想回乡又回不得,只好把离别阊门时潸然泪下的情景用各种方式留传给后代,聊解思乡之情。天长日久,苏州阊门的故事逐渐丰满,有枝有叶,在苏北平原广为流传。
四、移民在苏北的分布及数量
自称祖籍是苏州者,主要分布在扬州、淮安、盐城三个地区。移民到达的北部边缘,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西部基本上以京杭大运河为界,东部的南通地区基本不见。在这一地域范围内的今扬州、邗江、江都、泰州、姜堰、泰兴、高邮、宝应、淮安、灌南、沭阳、宿迁、泗阳、涟水、盐城、响水、滨海、阜宁、射阳、建湖、大丰、东台、新浦、东海、灌云等地皆有分布。从方言的现状和所掌握的文献资料来看,其中以姜堰、兴化、泰兴最为集中。响水、滨海、射阳、大丰的范公堤以东地区,明初尚未成陆,这里的苏州移民显然是在苏北地区二次或三次迁徙的。在这片地城范围内,自称是苏州移民后裔的至少在80%以上。明洪武年间,苏北地区接纳了如此之多的苏州移民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根据语言的现状基本上可以推断,这次移民的人数不可能占苏北当地当时人口的绝大多数。如果来自苏州(我们遵照习惯,把苏、松、湖、嘉、杭五府都称为“苏州”)的移民在苏北占绝大多数——这种来自一地,又集中移往一地,远远超过当地土著的板块式移民,新到一地后必然使用原地的方言。这样,苏北大地今天的方言应该是吴语,即使从语言发展变化的角度去考虑,至少也应该是掺有某些官话成分的吴语,而不是现在这样。仅仅是掺有吴语成分的官话。这个道理是十分浅显的,汉语方言的发展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事例。如南京、镇江的方言本来是吴语,演变成今天的江淮话,是永嘉年间大批移民所致。家谱、族谱和一些地方文献提供的资料证明,明初迁人苏北的移民并非都来自“苏州”。如兴化的《师俭堂李氏族谱》清楚地记载着被当地人称为“兴化阁老”的明代宰相李春芳家族明初由句容迁入兴化(有趣的是,李氏的后人也说是由苏州迁入)。民国《泰兴县志?卷二十四》载:“试征诸氏谱谍,大都皖赣各族。于元明之际迁泰。”泰兴的李、汪、尹、洪、施等氏族从安徽迁入。姜堰现在陈姓人口近6万人,有3支,其中2支来源于江西,只有一支来自苏州。此外,前文所引民国《泗阳县志》提及的吴氏也是来自句容,明代的卫所制是“留军屯田”。洪武年间,驻在苏北淮扬二府的军士及家属共约l2万人,这在当时的苏北人口中也占一定的比例。我们把这些情况弄清后,就可以对明初苏北接纳苏州移民的人数进行估算了(统计人口时,在缺乏文献直接记载的情况下,运用各种相关资料进行推算称为估算。“估算”这个概念是梁仲方先生在编写《历代人口田赋表》时首先提出并运用的并得到认可)。明扬州府辖江都、仪征、高邮、泰州、泰兴、宝应、兴化、如皋、通州、海门八县二州(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扬州市和南通市),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736165。其中仪征、如皋、通州、海门未徙人“苏州”移民,我们按平均数计算,假定移民占徙入县人口总数的50%,扬州府则徙入苏州移民220850人;明淮安府辖山阳、清河、盐城、安东、桃源、沭阳、海州、邳州、宿迁、睢宁、赣榆(地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淮安市、盐城市、徐州市和连云港市的一部分),洪武二十六年有丁口632541,其中赣榆、邳州没有移民徙人,宿迁、海州只有部分地区有移民徙入。我们以三个县没有移民徙入估算,仍按上述估算方法推测,淮安府接受移民 230000人。这样,明初苏北大约接收了共45万苏州移民,占当时总人口的34%左右。事实上。各县按纳的移民人数绝不可能达到与土著相等的人数,也不可能达到总人口的50%,我们的这种估算是最宽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