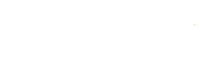宰信
露易丝·格丽克:诗人的教育
日前,露易丝·格丽克新作《合作农场的冬季食谱》(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出版,这本诗集仅15页,封面是八大山人的《稚鸡图》。在同名诗作中,格丽克写道,“每年冬季来临,老人们走进树林/采集苔藓,它们生长在/某些杜松子树的北边。/这是个慢活,要花很多天,尽管/因为光照减少,日子很短,/当他们的包装满后,就吃力地/回家去,苔藓太重了,很难搬。/妻子们让这些苔藓发酵,一个耗时的工程,/尤其是对这么老的人来说,/他们出生在另一个世纪。/……在厨房里,三明治被包好待市。/我的朋友过去常做这份工作。/胡丽松丽,我们的老师这样叫她,/给予照顾。我记得/看着她:在门内,/照章在卡片上写汉字,/按顺序翻译为相同的东西,/以及在下面:我们从起源处剥夺了它们,/如今它们开始需要我们了。”
露易丝·格丽克
《冬季食谱》是其第13本诗集,前12本诗集中主要有《阿喀琉斯的胜利》(The Triumph of Achilles)、《野鸢尾》(The Wild Iris)、《草场》(Meadowlands)、《阿弗尔诺》(Averno)、《村居生活》(A Village Life)、《忠诚与善良之夜》(Faithful and Virtuous Night)。除了诗歌之外,格丽克还有两本散文集行世,《证明与理论:诗歌札记》(Proofs and Theories:Essays on Poetry)、《美国原创性:诗歌札记》(American Originality:Essays on Poetry)。今年年中,格丽克还出版了《诗选集:1962–2020》(Poems:1962–2020),此前她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选集,《诗选集:1962–2012》(Poems:1962–2012)。
格丽克以自然的语言和深邃的视域而著称。方商羊认为,格丽克以天赋的能力,以深远的视界,将宏大的主题带到了我们的面前。“在格丽克中后期的作品中,她的音色中有一种威严的绝望,绝望而非沮丧,前者是在周遭黑暗的重负下获得智识上的启示,而后者则是仍存留于肉体或物质深处的负荷。这种绝望的后果是对现实世界的分离,从某个方面来说,即精神的短暂自由。”格丽克不关心美,只在乎真理,在《反对真诚》(Against Sincerit)中,格丽克写道,“一个艺术家的责任是把真实转化为真理。”而与此相连的,格丽克视诗歌为书面的,而不是口语的。诗歌不是真实的口和耳的交流,它是发送信息的头脑和接收信息的头脑的交流,格丽克对《美国诗人》(American Poet)说。
格丽克想用“调性”来替换“事实”,格丽克对《诗人与作家》(Poets & Writers)说,“对我而言,最要紧的是调性——心灵在进行冥想时的运行方式。那是你追随的目标。它引导你,但也让你迷惑,因为你不能将它转变为有意识的原则,或者确切地说出它的属性。你一旦将调性转变为有意识的原则,它就死了。它必须在你看来一直是神秘的。[……]诗歌的意趣在于调性,做出重大声明的调性,而不一定在于声明本身。人们常常从调性来细察作品里的声明,调性有时会显露出作者对一些言说内容的反对态度。”但格丽克无疑坦诚了一种特别的难度,它或许仅属于文学范畴,但也越来越与其他范畴联系在了一起。调性是否真实的,它的真实性是否带有一种特别的拒绝和阻抗,而它的弥漫又在多大程度上创造了一个没有广阔性的状况,在这个状况里,文学既是唯一者,又是没有者。
《合作农场的冬季食谱》
只有在沉默中,格丽克才感觉到,自己是专家。她对《华盛顿广场评论》坦承了这一点。而这样的沉默绝不是普普通通的沉默,而应当说是从不孕育生机和活力的沉默。她一生中都在忍受这种令人痛苦的沉默。这些沉默的时光,通常开始于一段欣喜若狂的尾声,继之以新的沮丧、挫败。她当然会尝试所有自己能够触及的方法,但她很少真正成功过。其中的恐怖与解放,百般折磨着她,但她也无法从这个局面中完全挣脱掉。第一次出现这种状况大概是在《初生》(Firstborn)出版后不久,大概有几年时间,格丽克栖身在空白的纸张中间,最后她不得不接受了一个事实:艺术不是她的专利。类似的挣扎和困扰,最后似乎都以释然和接受收场。
除了单纯的写作之外,格丽克用了大半生时间从事教学和编辑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对其文学的帮助或许尤其大。她最早任职于新英格兰烹饪学院,该学院为前夫约翰·德拉诺与其同仁筹建,后来又任职于威廉姆斯学院、耶鲁大学。从2004年到2010年,格丽克主持“耶鲁青年诗人奖”,先后遴选出七位青年诗人,依次是理查德·西肯(Richard Siken)、杰伊·霍普勒(Jay Hopler)、杰西卡·费舍尔(Jessica Fisher)、费迪·茹达(Fady Joudah)、阿尔达·科林斯 (Arda Collins)、陈恳(Ken Chen)、凯瑟琳·拉森 (Katherine Larson)。格丽克与上述诗人进行了大量的交流,某种意义上,格丽克帮助他们抵达了诗的完成。在其盛年,格丽克又经常去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爱荷华大学、波士顿大学等名校驻留或者授课。
在回应《美国诗人》(American Poet),格丽克坦诚了这一点。年轻作家的信仰、文学、激情,是格丽克极其重要的燃料。她甚至说,她在喝他们的血。格丽克热切地感受到,她作为作家的活力和变化,很大程度要归功于,沉浸在年轻人的作品中,甚至是那些极度陌生的作品。彼得·斯特雷茨福斯(Peter Streckfus),就是一位令格丽克沉浸的诗人,有一段时间,格丽克陷溺其中,仿佛戴了魔咒。有一次,格丽克还发现了,自己从彼得·斯特雷茨福斯那里偷了一首诗。
回到最初,格丽克在8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曾说,“从一开始,我就偏爱最简单的词。让我着迷的是上下文的多种可能性。我所回应的,在书页上,是一首诗如何借助一个词的安排,通过时间设定和节奏的微妙变化,接放这个词的丰富而令人惊讶的意义分布区。对我来说,似乎简单的语言最适合这种创新事业。”而在《证明与理论:诗歌札记》中,格丽克称写作是对语境或背景的寻找,诗歌会将与其强相关的被感动的局面带到作者面前,当然它不一定带到读者面前。而随着这些语境的衍生,格丽克被带到了一个新的境遇:她必须完整地面对世界,她必须创造完整的诗歌,组诗、诗集,她创造了“组诗体”(Book·length Poetic Sequence)。“我把这本集子(《阿勒山》(Ararat))整合出来的时候,我震惊于其内部的经纬。我不是有意识地嵌入那些重复或者呼应的表意动作和小插曲,而是它们就在那儿——这里有火车,那里又有火车,火车就成了一个角色。”格丽克对《诗人与作家》(Poets & Writers)说。
格丽克于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祖父是匈牙利犹太人,父亲是有文学抱负的成功商人,母亲是家务总管式的道德领袖、政策制订者。父母自小鼓励她发展自己的天赋和想象。也就是说,从小时候开始,格丽克就浸泡在融合的英语文化中。对于古希腊罗马文化、天主教文化、犹太人文化,格丽克可以说是信手拈来,如数家珍。“一个儿童就能意识到那伟大的人类主题:时间,它哺育了失落、欲望、世界的美,”她说。作为一个读者,格丽克偏好私密的窃听。她选择成为伟大诗歌的窃听者,而非“知心好友”。她装扮成布莱克的小黑孩、济慈的活着的手、艾略特的普鲁弗洛克。遥远的巴别塔、神秘的青铜器,在她的脑袋里胡乱地奏明。她当时就迫不及待想成为真正的诗人。
少女时代的格丽克患上了厌食症,体重慢慢地往下掉,像现在的我们在青少年时期所经历的那样。后来的格丽克懂得这是通往确定的自我的方式。“厌食症证明的不是灵魂优越于肉体,而是灵魂依赖于肉体。”诗人自述。在父母的帮助下,格丽克接受了长达七年的精神治疗。他时断时续的参加学校。在这之前,她写的诗歌是狭窄的、中规守矩的、静止的,也是不染世俗的、神秘的。在接受治疗之后,她中断了诗歌的写作。“心理分析教会我思考。教会我用我的思想倾向去反对我的想法中清晰表达出来的部分,教我使用怀疑去检查我自己的话,发现(自己表达中自我下意识地)躲避和删除(的部分)。它给我一项智力任务,能够将瘫痪——这是自我怀疑的极端形式——转化为洞察力。”她以同样地方式学会了诗歌的写作。她不再把自我简单地投射到诗歌之中,这是很妨碍心灵的光芒的。正确的方法是,区分出浅层的东西与深层的东西,将浅层的东西过滤掉,留下深层的东西。说得容易,做到难。
1968年,格丽克的第一本诗集《初生》出版。她迅速受到了认可。在这之前,她先后在莎拉·劳伦斯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研修课程。在哥伦比亚大学,格丽克遇见了斯坦利·库尼茨(2000-2001年美国桂冠诗人),至此,她一生的诗歌都受其影响。这时的诗歌还有些稚嫩,人们在诗歌里看到了罗伯特·洛威尔、T.S.艾略特的影子。格丽克的特质还是显露了出来,高度的敏感的疏离。这种质感,正是我们阅读时感受到另一个自己存在的原因。当我们感知到这一点,情况通常会变得很有趣,而不是反讽和苦涩。从《下降的形象》(Descending Figure)开始,格丽克开始将自传性材料写入她凄凉的口语抒情诗里。这些自传材料来自于童年故事、家庭关系、失去,以及青春、性爱、婚恋,等等。据柳向阳分析,“这些自传材料逐渐变得抽象,作为碎片,作为元素,作为体验,在诗作中存在。”其实,诗歌本身就是自传。每一行诗歌都象征着每一寸肉。格丽克曾说:“把我的诗作当成自传来读,我为此受到无尽的烦扰。我利用我的生活给予我的素材,但让我感兴趣的并不是它们发生在我身上,让我感兴趣的,是它们似乎是……范式。”像很多女性诗人一样,格丽克常常会练习一种反常:反驳一种思想、制造一种不可调和。因为她熟知这一条古老的经验:艺术梦想不是主张已经知道的东西,而是要阐明已经被隐藏的东西。
后来的作品中,格丽克不再直接显现出爆发感,她变得更为浓缩、沉默。诗人茂盛的树体,变得苍老和寡言。尤其是在诗人经受过重大的变故之后,诸如父亲的逝世、婚变。当然还有,一首诗歌的失败,反反复复的练习、修订。有时候,为了让一首诗歌复活,格丽克常常会花很大力气。像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所说的:“您写作,折腾,写作,折腾,写作,折腾。”格丽克的诗歌最重要主题是死亡。死亡遍布于诗句之中。《阿勒山》(Ararat)便是诗人在父亲逝世后的作品,被德怀特·加纳称作是在过去25年美国诗歌的最残酷的书。在对死亡的缅怀中,在对创伤的超越中,我们见证了诗人对于生命的献礼。“我为一种使命而生,/去见证/那些伟大的秘密。/如今我已看过/生与死,我知道/对于黑暗的本性/这些是证据,/不是秘密——”
据熊辉介绍,格丽克最早进入中国是在80年代。1989年7月,由彭予翻译的《在疯狂的边缘:美国新诗选》出版,其中就有格丽克(路易斯·格拉克)的四首诗歌,《都是圣徒》《诗》《苹果树》《哀歌》。彭予认为,格丽克“深受自白派传统的薰沐,注重披露作为一个妇女的心情感受。她的诗使用的是一种朦胧,甚至支离破碎的风格,冷峭、幽密、笔调细腻,具有内在的凝聚力和艺术原生美。”
(部分译文参考:《合作农场的冬季食谱》(Winter Recipes from the Collective),姜巫译;《与露易丝·格丽克的问答》,许诗焱译,《世界文学》2021年第2期;《诗人之教育》,柳向阳译,《四川文学》2017年第1期。)
文学塞内加尔:从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到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
日前,本年度龚古尔文学奖(Le Prix Goncourt)揭晓。塞内加尔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Mohamed Mbougar Sarr)凭借《神隐的记忆》(La plus secrète mémoire des hommes)摘得了本届桂冠。萨尔的荣膺可谓实至名归。在本届评审过程中,萨尔在第一轮就赢得了全部评审团10票中的6票。龚古尔学院秘书长菲利普·克洛岱尔称其符合龚古尔文学奖的诉求和标准。龚古尔文学奖评审团成员保拉·康斯坦特(Paule Constant)盛赞了萨尔的新作,称其风格华丽,几乎是一部对文学的赞美诗。
穆罕默德·姆布加尔·萨尔
在龚古尔大约120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出现撒哈拉以南非洲作家获奖的情况。2021年也被戏称为非洲文学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布克奖、卡蒙斯奖、龚古尔文学奖、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Neustadt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Literature)、国际布克奖、德国图书贸易和平奖(Friedenspreis des Deutschen Buchhandels)都花落非洲作家或非洲裔作家。这其中,塞内加尔和塞内加尔裔作家又最为闪耀,除萨尔外还有获国际布克奖的塞内加尔裔法国作家达维德·迪奥普(David Diop)、获得纽斯塔特国际文学奖的塞内加尔作家保巴卡·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此前获得龚古尔文学奖的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也是塞内加尔裔法国作家。
在巴黎索邦大学教授非洲文学的泽维尔·加尼尔 (Xavier Garnier) 说,“欧洲文学界正在重新唤起对非洲的兴趣。”历届非洲裔获奖作家有勒内·马兰(René Maran)、玛丽·恩迪亚耶(Marie NDiaye)、莱拉·斯利马尼(Leïla Slimani)。此前,非洲国籍获奖者还有摩洛哥作家塔哈尔·本·杰隆(Tahar Ben Jelloun)、黎巴嫩作家阿敏·马卢夫 (Amin Maalouf)。除非洲外的非法国国籍的获奖者还有,比利时作家查尔斯·普利斯涅尔 (Charles Plisnier)、比利时作家弗朗西斯·瓦尔德(Francis Walder)、罗马尼亚作家温蒂勒·霍里亚(Vintilă Horia)、瑞士作家雅克·谢塞克斯(Jacques Chessex)、加拿大作家安东尼·梅耶(Antonine Maillet)、比利时作家法兰斯瓦·维耶尔冈(François Weyergans)。
前塞内加尔文化部长阿卜杜拉耶·伊莱曼·凯恩回应说,萨尔和他的作品是塞内加尔和整个非洲的骄傲。龚古尔公布后,萨尔在塞内加尔名声大振,此前他在塞内加尔就有足够的影响力。不久后,萨尔被授予塞内加尔国家勋章,此举似乎将其抬升到塞内加尔首任总统、诗人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的地位。目前,萨尔的作品在塞内加尔处于热销状态。
《神隐的记忆》
龚古尔文学奖揭晓后的11月7日,一年一度的非洲作家国际日(International Day of the African Writer)开幕,本年度活动在塞内加尔作家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Writers of Senegal)总部召开。非洲作家国际日,由泛非作家协会(Pan African Writers' Association)发起,至今已经举办到了29届。塞内加尔作家协会成立于1973年,历届主席是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阿密娜达·索·法勒(Amanita Sow Fall)、阿马杜·拉明·萨尔(Amadou Lamine Sall)、阿利乌内·巴达拉·贝耶(Alioune Badara Bèye)。贝耶称,萨尔是可以轻松应对权力、宗教、同性恋等话题的人。
萨尔出生于达喀尔,他是家中长子,成长于塞内加尔中西部城市迪乌尔贝尔。后来萨尔入读了塞内加尔最好的中学,圣路易斯军事学校,塞内加尔很多政要都出身于此。毕业后,萨尔抵达法国,他一心想做文学,他先进入Lycée Pierre d'Ailly,而后考取巴黎的社会科学高级研究学院,在这里,萨尔研究利奥波德·塞达尔·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不过其论文始终未完成。如今萨尔仍然希望回到校园中,他正在积极准备博士申请。现在,萨尔居住在博韦。从圣路易斯军事学校开始,萨尔就是痴迷文学,到了大学更是愈演愈烈,忘乎所以地投入文学创作之中。历数世界文学,萨尔喜欢的作家有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费尔温·萨尔(Felwine Sarr)、马利克·法尔(Malick Fall)、阿尔贝·加缪、让-保罗·萨特、桑戈尔。
迄今为止,萨尔已经出版了四部作品,其前三部分别为《圣城》(Terre ceinte)、《沉默的唱诗班》(Silence du Choeur)、《纯粹的人》(De purs hommes)。第四部作品《神隐的记忆》由于菲利普·雷伊出版社(Philippe Rey)与姬姆萨恩出版社(Éditions Jimsaan)合作出版,后者由布巴卡尔·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纳菲萨图·迪亚(Nafissatou Dia)和费尔文·萨尔(Felwine Sarr)等作家在达喀尔创办。在摘得龚古尔文学奖之前,《神隐的记忆》已经销售了多达3万册,未来它的销量将超过50万册,这大概是龚古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的销量。本书的版权已经被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出版社获取,有意大利的Edizioni E/O、沙特阿拉伯的Dar Athar、西班牙的阿纳格拉玛出版社(Anagrama)、德国的卡尔·翰泽尔出版社(Carl Hanser Verlag München Wien)、希腊的Patakis、以色列的Modan、瑞典的Bonniers。
《神隐的记忆》讲述的是迪加内·拉蒂尔·费伊(Diégane Latyr Faye)的文学生涯,他在读过T.C.伊莱曼(T.C. Elimane)的《非人的迷宫》(Labyrinthe de l'inhumain)后,开始了一个追寻和探索之旅,混杂着殖民主义、流亡文学、性爱、永恒言论。借鉴自波拉尼奥的作品,萨尔将侦探小说的元素扩大至极限,它收容了启蒙小说、情色叙事、哲学散文、新闻报道、诗歌、传记、讽刺诗、政治小册子……萨尔坦诚自己接受了波拉尼奥的影响,它以波拉尼奥的方式承接着令人不安的现实、斑斓的梦想、野蛮的大陆。
“T.C.伊莱曼是谁?”萨尔写道,他是殖民主义最成功也最悲惨的造物。伊莱曼想变成白人,他几乎要成功了,但他永远不是。伊莱曼比欧洲人更了解欧洲,但他被擦除了,被藏匿在纷争和历史的尘埃里。或者说,萨尔试图表明,在欧洲那个真理的场所,伊莱曼没有被准许有他的落座。伊莱曼的原型是马里作家扬博·乌洛格(Yambo Ouologuem),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子,勒诺多文学奖(Prix Renaudot)获奖者,他在获奖后不久陷入一场抄袭风波,他被控诉抄袭格雷厄姆·格林和安德烈·施瓦茨-巴特(André Schwarz-Bart) 。遁入非洲大地后,扬博·乌洛格变得籍籍无名,现实中的他一直活到2017年。在书中,萨尔感叹道,“像所有作家一样,我们实实在在地感受到了什么也得不到、什么也留不下的痛苦,说到底,我们批评的只是我们自己,我们表达的是对自己不入流的恐惧,我们感觉正置身于一个没有出路的洞窟,我们担心像老鼠一样死在那里。”
“反思历史、探讨当下与过去的关系是非洲法语小说的年度热点。通常,历史被视为对过去的客观重建,记忆则被认为从情感、爱与怨恨中孕育生成。文学虚构总是与历史保持着或远或近的距离,使历史与记忆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从阿尔及利亚到马达加斯加,从著名的历史事件到“沉默的历史”,非洲法语小说以虚构的方式重建历史,同时对当下与殖民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主观探察,体现出文学特有的认知能力。”李征在《“以虚构挑战真实”——2020年非洲法语文学综论》一文中表示。李征梳理了非洲法语文学的三个新动向:关注文学形式上的实验与探索,如法属留尼汪等地的“断片之书”或“散书”;关注作品内容传递的声音;关注文学的跨文化性,如盖勒·贝雷姆(Gaëlle Bélem)的《门后有妖怪》(Un monstre est là,derrière la porte)对法语、克里奥尔语、拉丁语、阿拉伯语、马约特语的混杂。
塞内加尔位于萨赫勒地区的最西端,萨赫勒地区是指撒哈拉沙漠以南的边缘地带,自古以来,塞内加尔就是非洲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历史上,塞内加尔曾被法国殖民,至今,塞内加尔仍保留法国殖民时期的痕迹,比如语言、教育、传媒等等,比如法国主要的报纸和杂志都会在塞内加尔发行。1958年,塞内加尔实现自治,1960年,塞内加尔独立,桑戈尔任首任总统。塞内加尔最好的大学是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Université Cheikh-Anta-Diop),部分时期称作达喀尔大学,它的前身是法国黑非洲学院(Institut Français d'Afrique Noire)和法属西非医学院(École de médecine de l'AOF)。谢赫·安塔·迪奥普是非洲中心主义的代言人,其主要著作是《黑人民族与文化:从埃及古代黑人到今天黑非洲的文化问题》《黑非洲的文化统一性》。谢赫·安塔·迪奥普大学内设立有黑非洲基础研究院(Institut Fondamental d'Afrique Noire)。
目前看来,撒哈拉沙漠以南非洲现代文学以塞内加尔最为繁荣。多重历史和因素促成了塞内加尔文学的繁荣,这其中,首任总统桑戈尔功不可没。1948年,桑戈尔领导塞内加尔从法国殖分裂出去,组建了塞内加尔民主阵线(BDS)。此后,他带领塞内加尔人民实践了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社会主义。除此之外,桑戈尔还是第一位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的非洲人。桑戈尔的主要论著有五卷本《自由》(Liberté),以及《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Anthologie de la nouvelle poésie nègre et malgache de langue française)、《埃塞俄比亚诗集》(Éthiopiques)、《红狮》(Le Lion rouge)等。
1934年,桑戈尔和法属圭亚那作家莱昂·达马、马提尼克作家艾梅·塞泽尔创办了《黑人大学生》(L'Étudiant noir),后续《黑人大学生》还吸纳了乌斯曼·塞姆班、比拉戈·狄奥普两位塞内加尔作家加入。三位诗人相继出版了自己的代表诗集,达马斯的《色素》(Pigments)、塞泽尔的《返乡笔记》(Cahier d'un retour au pays natal)、桑戈尔的《影之歌》(Chants d'ombre)。其中,由《返乡笔记》引申出了黑人性(négritude)概念,后来成为三位诗人、作家的代名词,黑人性也是二十世纪非洲文学的重要节点。
黑人性受造于人类学研究,但归于文学却有几分暧昧不明,桑戈尔将其粗浅地定义为,黑人世界的文化价值的总和。黑人性鼓励作家回归和珍视非洲传统,以及非洲文学的古老源泉,如桑戈尔所言,“当今最优秀的黑人艺术家与作家,有意无意,都受到黑非洲文明之精神的激励,无论他们来自非洲还是美洲”。同时,黑人性也揭示出了非洲文学的风格与特质,比如注重意象与节奏的表现。亨利·路易斯·盖茨(Henry Louis Gates Jr.)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他的喻指理论,喻指即土语,喻指理论突出非洲文学和黑人语言的即兴、幽默、尖刻、颠覆性。
1948年,《黑人和马达加斯加法语新诗选》发表,萨特旋即撰写了书评,《黑皮肤的俄尔甫斯》(Orphée noir)。萨特对外宣告,“从前手握神圣权利的欧洲人,也已经在美国和苏联的注视之下感觉到了某种失势;现今欧洲不过是一个地理意义上的意外罢了:一个被亚洲推到大西洋去的半岛。欧洲人曾寄希望于自己的伟大———至少还能在非洲那些驯兽的眼里被折射出来。但如今这样的驯兽之眼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狂野而且自由的面孔———正在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萨特充分肯定了黑人性的价值,但他也认为黑人性有“反种族的种族主义”(racisme antiraciste)的嫌疑,正如沃莱·索因卡所批判的那样。“一个黑人不能否认他是一个黑人,也不可以宣称他是某个抽象的无色人种的一部分:因为他的皮肤是黑色的。也由此,他有了那些被侮辱、被奴役的史实作为后盾:他背负起如投掷向他的石块一般背负起“黑鬼”的称号,再次昂首挺立,面对白肤之人而骄傲称自己为黑肤之人。联合最终会来到,把在这一斗争中所有被压迫的人民团结在一起,我称之为分离和否定的时刻将最早出现在殖民地之上:这个反种族的种族主义将会是通往废除种族差异的唯一道路,别的道路则全无此可能。[……]他开始流放,一个双重的流放:肉体的流放给他心灵的流放提供了一个宏伟的图景;他绝大部分时间都待在欧洲,在那寒冷和乌云笼罩之中;他梦想海地的太子港,但当他身处太子港之时却已身为一个被流放之人;奴隶商人把他们的父辈从非洲带出来,继而贩卖到各个地方。这本书里所有的诗,除去那些在非洲被写下来的,都向我们展示了同一种神秘的地貌。一个半球;在其最显著的位置中形成三个同心圆。最外圈是扩展了的流放之地,无色的欧洲;中间是令人眼花缭乱的群岛和幼年时代这一圈,它们围绕非洲跳旋风舞;最后一圈是非洲[……]黑人性是自恋的胜利和水仙的自杀,是那超越了文化、语言和所有心理事实的灵魂的张力,是未知的明亮的夜、是对于不可能有意识的选择,是巴塔耶所称的酷刑,对世界直观的接受和以心之律的名义对于世界的拒绝;有着双假设矛盾(double postulation contradictoire),要求甚严的撤回(rétraction revendicante)以及慷慨的扩张(expansion de générosité)的黑人性在其本质上原是诗歌。终于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革命设想和最纯净的诗歌发自同一源泉。”
接续桑戈尔的是阿里乌纳·狄奥普(Alioune Diop)和他主办的《非洲存在》(Présence africaine),通过这本杂志,黑人性的概念传播到了非洲大陆的深处。《非洲存在》依托巴黎和达喀尔两地,其受众主要是两地的黑人精英群体,《非洲存在》还发展出了一个叫做非洲存在的出版社,《南方小说》(Nouvelles du Sud)、《黑人-非洲人》(Peuples Noirs-Peules Africains)则是《非洲存在》的后继者。《非洲存在》的辉煌和成果几乎是不可复制的,它可以说是现代黑人运动的最早的圆头之一,同时,它也是50、60年代的黑人文学的民族主义先遣队、世界主义中转站。理查德·赖特(Ricahrd Wright)等一批卓越的黑人作家和知识分子都曾是《非洲存在》的撰稿人。
除上述重点提及的作家之外,塞内加尔重要的作家还有,诗人大卫·迪奥普(David Diop)、“兔子传统”民间文学弘扬者比拉戈·迪奥普(Birago Diop)、作家兼导演乌斯曼·塞姆班(Ousmane Sembène,旧译桑贝内·乌斯曼)、作家兼女权主义者玛利亚玛·芭(Mariama Bâ),以及上述简略提及的作家兼政论者保巴卡·鲍里斯·迪奥普(Boubacar Boris Diop)。他们的代表作分别是《捣蛋人士》(Coups de pilon)、《听阿玛杜·库姆巴讲故事》(Les Contes d'Amadou Koumba)、《哈拉》(Xala)、《一封如此长的信》(Une si longue lettre)、《穆兰比:枯骨之书》(Murambi, le livre des ossements)。保巴卡·鲍里斯·迪奥普的Doomi Golo是目前仅有的沃洛夫语小说之一。
(部分译文参考:《黑皮肤的俄尔甫斯》,蒋思洁译,《西部》2017年第6期。)
责任编辑:臧继贤
校对:张艳